1616年,约翰·史密斯所著的《新英格兰状况》(A Description of New England)初版前言中,有多篇向这位船长的发现致敬的诗歌,其中有一篇出自诗人和讽刺作家乔治·威瑟(George Wither)之手。威瑟对史密斯的探险活动表示了祝贺,预言由英国人占有的美洲“花园”可以轻易产出难以估量的自然财富:
与其节俭度日、自降身价,不如花费一点时间
去那尚未开垦的花园,去感受新英格兰的风貌,
富裕丰饶在等着我们
去整理自然的硕果;
今天的美好预示着来日的希望,
去那富饶的王国,修复时间和傲慢
带来的衰朽吧。广阔的西部犹胜
英格兰血脉已经占有的土地。
史密斯笔下新英格兰的自然资源为威瑟的观点提供了支持。史密斯主张,新英格兰的环境“财货丰足”,不需要迁居移民付出多少力气。他写道:
这是一处逍遥的天然宝地,能让我们过上在英国要么过不上、要么耗费巨资才能过上的自由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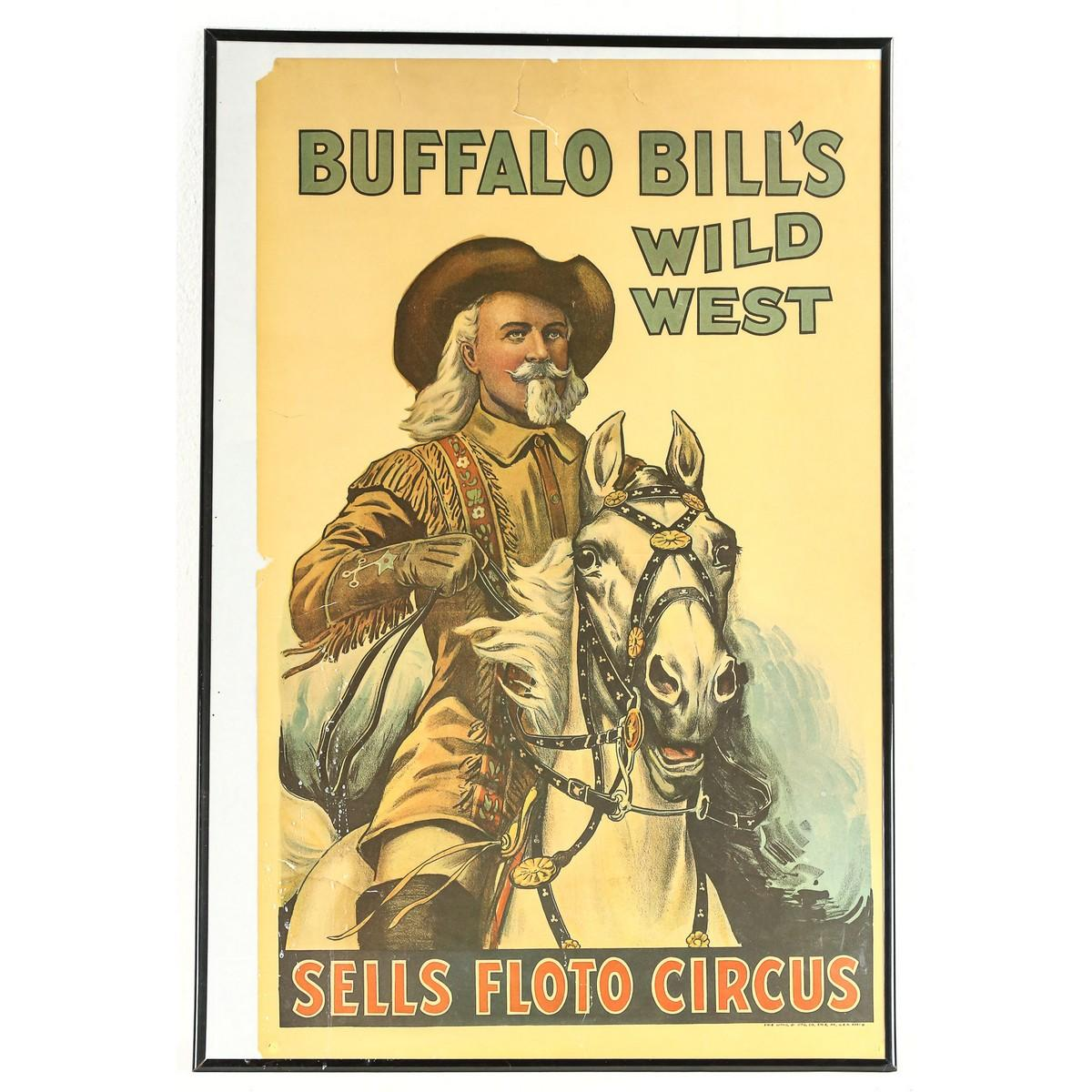
新英格兰的森林里能抓到狸、獭、貂之属,还有黑狐,它们的毛皮有利可图,尤其是“如果能排除法国人参与贸易的话”。新英格兰的水域产鱼,足够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童”一天杀死上百条鳕鱼,经过加工晾晒,一百条能卖10-20先令。史密斯问道:“这个收益难道不能让仆人、主人和商人满意吗?”尽管这位船长承认,只有赚钱的希望才能促使英国人放弃熟悉的环境、前往未知的领域,但他并没有只讲有利可图的美洲动物。在史密斯的想象中,可随意取用的丰富美洲生物会吸引潜在的殖民者定居新英格兰。“有胆有识,身体健康”的探险家能够为两三百人供给“应有尽有的优良谷物、鱼类和兽肉,同时又能让劳作成为乐事”。水下、空中、地上有无数种动物,可以供移民享用。最重要的是,这种“不可思议的丰饶”每年都会增长,并且“无人开发”。按照史密斯的看法,不管是作为给养、生计还是消遣对象,新英格兰的丰富动物资源都为英国殖民者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们有希望得到远胜于国内的物质条件。
史密斯盛赞新英格兰的动物宝库及其能够为移民带来的好处,这体现了英国殖民文本的第二个显著特征。评论者迅速从讲述初遇经历转向殖民宣传,这是一种特殊的英语文体,目的是吸引投资人,尤其是移民参加美洲殖民项目。动物丰饶的传说变成了广告,殖民宣传家们鼓励人们移居到一系列陌生的环境中——从大西洋海岸一直到太平洋海岸。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美洲环境经历得多了——观察者与写作者也多了——本土动物为移民服务的展望也更加宏大了。最显著的是,殖民宣传家们开始将两件事联系起来:一件是无主、待开发的野外生物,一件是每个新边疆都会有的自由观念,这种观念有敉平阶级的作用。殖民者相信,大众皆可利用美洲自然资源的诱惑会推动英裔美洲移民的发展,从而将英属美洲的领地向西拓展。由此,“野外生”为移民定居提供了保障。
与最早期强调潜力的记述不同,17世纪的作者对北美环境的描绘不吝辞藻,盛赞包括野外生物在内的自然资源,其目的明确,就是为了吸引移民和投资人。英国殖民宣传家以丰富的野外生物为据,证明当地生态环境富足,适合移居。但他们也指出,面对新环境的殖民者需要从整体上反思自己与动物的关系。这是一个没有家畜的世界,鹿群可以理解为与牛群类似。这些作者提出,美洲原住民占有和穿戴鹿皮,而英国人定居点周围也有鹿群,这些都证明殖民者可以利用这些资源保障家业、组建家庭、塑造地方经济,条件远远好过他们在资源枯竭的欧洲所希望达到的程度。
随着17世纪的殖民者与美洲生态系统之间发生交互作用并开始消耗野外生物资源,评论者拓展了先前的预测,坚称本土动物还能以更多的方式为移民提供支持。殖民宣传家们从先前的记述中取出一页,然后列出长长的表格,罗列了美洲的生物及其用途。野兽可以为定居和探险提供物资,能产生新的家畜品种、猎物、药物和可售卖的商品,这些都有助于将土地推介给未来的移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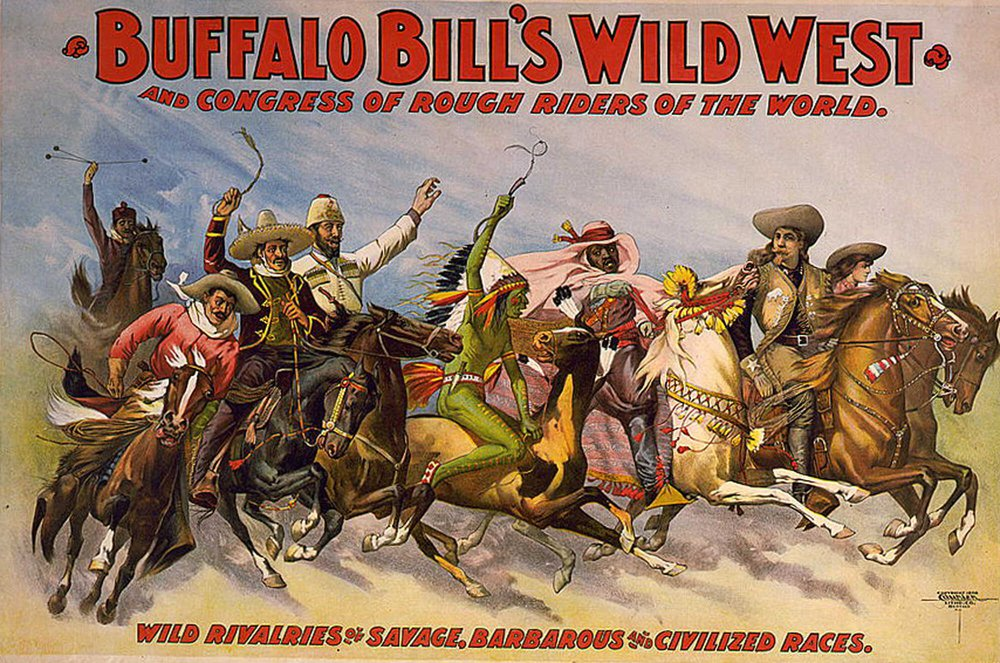
殖民宣传家们展现了美洲的自然财富是如何远胜于英格兰的。1602年,约翰·布里尔顿记述了楠塔基特岛(Nantucket Island)生活着“许多鹿和其他野兽,从足迹便可看出”,全岛遍布“大量野鸟”——证明相比于美洲自然环境的富饶,“全英格兰最肥沃的土地(本身)也显得贫瘠”。1609年,亨利·斯佩尔曼(Henry Spelman)撰写了《弗吉尼亚记》(“Relation of Virginia”)一文,宣称这片土地有大量“鹿、羊、熊、狼、狐、麝猫、野兔、飞鼠”和其他哺乳动物,还有“大量鸟类”和“丰富鱼类”。弗吉尼亚理事会成员宣称:当地哺乳动物、鱼类和鸟类“丰富繁多,举世无双”。
英国作者还说明了个别物种优于欧洲同类。有一位评论者写道:新英格兰的野火鸡“比英国的火鸡大得多,也更加甘肥鲜嫩”;新英格兰的森林里有“好几种鹿,有的一次能生三四胎,这在英格兰可不常见……还有一种大型野兽,名叫麋鹿(Molke),体型不亚于公牛”。宣传家感叹道:如此富饶的土地“完全无人占用,而英国有那样多的诚实男子和他们的家人,地狭人稠,生活艰难”,实为“一大憾事”。还有谁更适合“利用这片富饶的土地呢”?
在试图推销一个陌生的、基本不为人知的环境时,殖民宣传家急于向潜在的移民保证,他们无须害怕数量庞大的野兽。甚至在16世纪对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的描述中,作者们就倾向于否定当地动物是危险的,以免打击殖民者的积极性。尽管帕克赫斯特承认大西洋沿岸北部的熊生性凶猛,却坚持说它们“绝对不会主动伤人,除非受到攻击”。哈里奥特也这样认为,他写到弗吉尼亚的熊通常“一看见人”就跑。也有观察家持批评态度,给连篇累牍吹捧北美环境降了降温,以只言片语告诫人们注意不那么美好的野外生物。1630年,伍德在一份宣传文章的前部分列出了新英格兰的各种货品,后面就罗列了各种毒物,包括蚊子和“颜色诡异,体型巨大的蛇和蟒”。按照伍德的看法,蛇、蛙、飞虫和狼是“当地最恶劣的东西”。
英语文本极力夸赞美洲地貌,却对林居野兽带给殖民者的危险轻描淡写,将动物描绘成善意的存在。伍德坚称,狼是“当地最大的不便因素,包括对个人的伤害,也包括对当地整体的危害”,尽管没有狼曾“袭击过一个男人或女人”。马和奶牛都是安全的,只有山羊、猪和牛犊会被狼侵害。史密斯承认,尽管新英格兰乍看上去是“一个先让人害怕、后让人喜爱的国度”,但这些看似“荒芜的岛屿”依然有着丰富的“水果、鱼类和鸟类”。在史密斯看来,大量有用或无用的野外生物表明美洲“内陆很可能……十分肥沃”,因此非常适合人类居住。宣传家向读者保证,总体上讲,当地的“不利因素”充其量只是小麻烦而已。
17世纪和18世纪的英国殖民者依然对动物性商品有着浓厚兴趣,但他们的预设是要与美洲原住民合作贸易。在殖民者心目中,17世纪发展起来的跨大西洋毛皮贸易不过是印第安人原有经济往来关系的一个变体,因为本土居民之间本就有毛皮交易。一份1602年的弗吉尼亚北部探索记讲述了英国探险家与美洲原住民的早期贸易交往。据布里尔顿回忆,印第安人献出了“狸、獭、貂、獾和野猫的皮……大张鹿皮、海豹皮和其他我们不了解的兽皮”。伍德提到了英国殖民给新英格兰本土经济带来的变化,美洲原住民过去一直在猎杀“狼、野猫、浣熊、河狸、水獭、麝猫”,但殖民者到来后,印第安人将“它们的皮和肉都卖给了英国人”。
在17世纪,殖民宣传家开始描绘美洲食物丰富的形象,以此吸引国内食不果腹的下层阶级。到了自然丰饶的世界,阶层差异即便不会失去意义,至少不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史密斯坚称,不管一个人的地位如何——不论是“仆人,主人(还是)商人”——他每周只需劳作三天,就能在新英格兰捕到“吃都吃不完”的丰富鱼类。通过这种“美妙的娱乐活动”,“木匠、石匠、园丁、裁缝、铁匠、水手、锻工等”都能获取生计所需的一切食物。之后,殖民者还可以将吃不完的鱼卖掉,或者与“渔民、商人”交换“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
殖民者主张:辛勤耕作,再加上“当地丰富的鱼鸟瓜果”,能够为移民提供充足的物资。事实上,约翰·哈蒙德(John Hammond)写道:切萨皮克显然“不可能缺食物”,“因为河流与树林足以供养”。鹿肉在英国受到追捧,因此其在北美南部各殖民地的广告中占据突出位置。在作者笔下的家庭中,鹿肉和面包一样是餐桌上的主食,从而显示美洲平民能够享受到本土士绅的待遇。1666年,罗伯特·霍恩(Robert Horne)宣称,卡罗来纳的鹿和野火鸡甚至比英国品种“口味更好”。野外生物保障了民众有获取生活必需品和珍馐美食的渠道,因此殖民地的社会分层程度会低于英格兰,就连最穷的人都能过上舒适的生活。
宣传家还提出,由于美洲动物繁多,殖民者可以享受过去专属于上层阶级的其他特权。人人都可以钓鱼、打猎取乐——这与英格兰形成了鲜明对照,那里的娱乐性狩猎基本局限于有产者和有社会地位的人士。按照史密斯的看法,新英格兰的捕鱼活动为所有人提供了“雅乐”和生计以及贸易,前往新殖民地的先生们还可以享受捕鸟的快乐。在史密斯描绘的画卷中,“森林河湖”为“所有喜欢打猎的人提供了充足的猎物,还有野兽可供狩猎”。森林里的野外生物奉上“身体作为可口的食物”,而且它们的兽皮“如此昂贵,以至于劳作一天的报酬抵得上船长的工资”。
史密斯的预言在宾夕法尼亚应验了。17世纪末,加布里埃尔·托马斯(Gabriel Thomas)注意到,移民们“以狩猎、捕鱼和打鸟为娱乐休闲,尤其是在有名的大河——萨斯奎汉纳河(River Suskahanah)两岸”。他声称当地有多种现成的“利润丰厚、肉质鲜美的”野兽,其中就包括鹿,鹿肉“在大多数和善求新的人看来,美味至极,远胜欧洲”。

18世纪,宣扬英裔美洲人西进殖民的作者们有两个世纪积累的殖民文本可供参考——这些文字已经将繁多的野外生物转化成了一种殖民宣传的比喻。到了这个时候,宣传文稿中早已大肆宣扬过野外生物对殖民者的益处,在早期英裔美洲定居点中也得到了相应的实践。18世纪的作者们在评述新区域和新边疆时可以更加自信地断言,野外生物能维持殖民者西进占地的生活。在这百年间,殖民者一直在设想各种本土动物的用处——生计、商贸、娱乐——但总是将本土动物理解为一种殖民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方案注重通过移民机制来实现占有。
18世纪初,博物学家约翰·劳森和约翰·布里克尔(John Brickell)将鱼、野鸟和鹿肉算作北卡罗来纳种植园主的重大优势。事实上,由于人们只需要“一般勤奋”就能获取“所有必要生活物资”,这意味着“不会有四处游荡的乞丐盗匪”,而在英格兰,这些人则随处可见。种植园主将大量鹿皮出口到英格兰和其他地方,于是鹿皮成了“北卡罗来纳提供的优良货品之一”。劳森声称,就连“出身低微”的移民都会迅速致富。罗伯特·贝弗利(Robert Beverley)表示,在弗吉尼亚边界,狩猎“熊、豹、野猫、麋鹿(和)野牛”都“为猎人提供了利益和娱乐”。1770年,乔治·米里根-约翰斯顿(George Milligen-Johnston)复述了贝弗利观察到的现象,写道:南卡罗来纳的野鸟、兔子、浣熊、负鼠和鹿为当地种植园主提供了“健康的锻炼和极有趣的消遣”。约翰·菲尔森(John Filson)预计,在阿巴拉契亚山脉对面的更西边,野牛会为肯塔基人提供牛肉和制革用的牛皮。
独立战争后,美国评论员发布了科学陈述与夸大宣传成分不相上下的广告,吸引移民去新获得的西部土地,还有持扩张主义的政客们希望获得的土地。吉尔伯特·伊姆利(Gilbert Imlay)的《北美西部地理志》(Top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the Western Territory of North America)首次出版于1792年,书中有对阿巴拉契亚山外风物的现实记述,也有称颂肯塔基自然环境富饶的赞歌。在这片西部边疆——伊姆利在此地做了多笔土地交易,希望借此牟利,其中有一些交易见不得人——富有冒险精神的殖民者能够享受狩猎野外生物的快乐:
它们无忧无虑地漫游,俨然是这里的主人。天啊!多么自由,多么迷人啊。
5年前,牧师、议员、土地投机商梅纳西·卡特勒(Menasseh Cutler)发现西北领地的动物界,举世无双。大地上到处游荡着无数动物,胜过“美洲旧殖民地的任何区域”。另一位18世纪末的作者宣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土地“甚至比传奇还要传奇”,这里是一片“受自然垂爱……最是逍遥”的土地,俨然“完美的天堂”。
19世纪,探险家与旅行家的记述,再加上投机者撰写的越来越多的宣传文稿,共同详细讲述了无数野外生物能为美国西进殖民提供的种种支持。1806年至1807年,泽布伦·派克(Zebulon Pike)对美国西南部开展考察,考察队发现了大群野牛、麋鹿和羚羊,以至于队里的记录者写道:“一个猎人无疑就能养活200人。”1816年,亨利·科尔(Henry Ker)写道,美国西南地区的“丰美水草供养着成群的鹿和牛”,尽管“它们依然野性难驯”。科尔则抱怨道:这片“优良土地”居住着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宣称它属于自己,其根本“没有勤劳之人培育”。科尔对两者都持批判态度,他写道:
一群无理之徒占有了本能为文明民族带来巨大价值的土地,实在遗憾。
其他作者阐述了西部平原上的野牛何以是“对旅者最重要的草原动物”,同时美国商人也很看重这种大型动物,因为用它能做出雪橇缰绳、肉、脂肪、火药筒、帽子和长筒袜。19世纪的指南书向移民保证,尽管西部荒原野兽盛行,但没什么好怕的。一篇文章宣称“就连最胆小的人也无须拖延”,因为熊、狼之类的野外生物怕人,绝对不主动伤人。
但在殖民者的想象中,本土动物并不仅仅代表物产财富。作者们将边疆的特质赋予了本土动物,在其无主的经济意义上,以及身体不受束缚的层面上,野外生物都是自由的。独立战争前的英国宣传家强调前一个方面,提出免费获取的动物资源预示着美洲的社会结构会更加平等,任何“出身低微”“一般勤奋”的人都能致富。独立战争后,动物的身体自由与殖民文本中的一个主题产生了更强烈的共鸣。1826年,蒂莫西·弗林特牧师(Rev. Timothy Flint)就指出了这一点。他写道:“很少有人殖民仅仅是为了寻找更优良、更廉价的土地。”实际上,他们是为了——
新土地上更美丽的森林与河流、更温和的气候和鹿鱼鸟兽,以及种种赏心悦目的形象带来的观念,它契合着新土地上无拘无束的野性生活。
弗林特推测,这种“想象力的影响”,再加上“无穷无尽的广告”对“移民产生了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这正是宣传家希望传递的信息。殖民者对野兽的印象是由“野性”和“自由”这两个概念建构起来的,进而又将这些观念化为边疆移民的希望。如此一来,野外生物标定了英属美洲边疆作为自由之地的属性。

(本文摘自安德里亚·L.斯莫利著《天生狂野:北美动物抵抗殖民化》,姜昊骞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7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