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是神话中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其影响力由于浪漫瑰丽的星座想象而经久不衰,被视作中国本土的“情人节”。实际上七夕所对应的牛郎织女星象,早在先秦时代就有所记载:“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这段诗歌出自《诗经·小雅·大东》,是最早对牛郎织女星象的艺术性创作。不过与我们如今所熟知的牛郎织女传说不同,《大东》止于将星座拟人化,尚未给出其中的联系;其所想要表达的内涵也与爱情无关,而是借星象无法为人民分担劳作的苦痛来怨刺劳动人民饱受压榨的现实。
可见,在创作《大东》的时代,牛郎织女星尚且没有与爱情的神话故事编织在一起,其所代表的仅仅是作为劳动人民的男性和女性形象。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在《诗经》这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中,七夕传说的雏形无迹可寻呢?也不尽然。在我们所知悉的传说故事结局中,牛郎织女被人为地分隔于银河两侧,一年仅能相见一次,如此赋有悲情色彩却兼具浪漫的结局,恐怕并非完全出自先人的想象,而是有相对应的社会现实支撑。在法国社会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所著《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之中,就通过对《诗经》的解读,揭示出这种社会形态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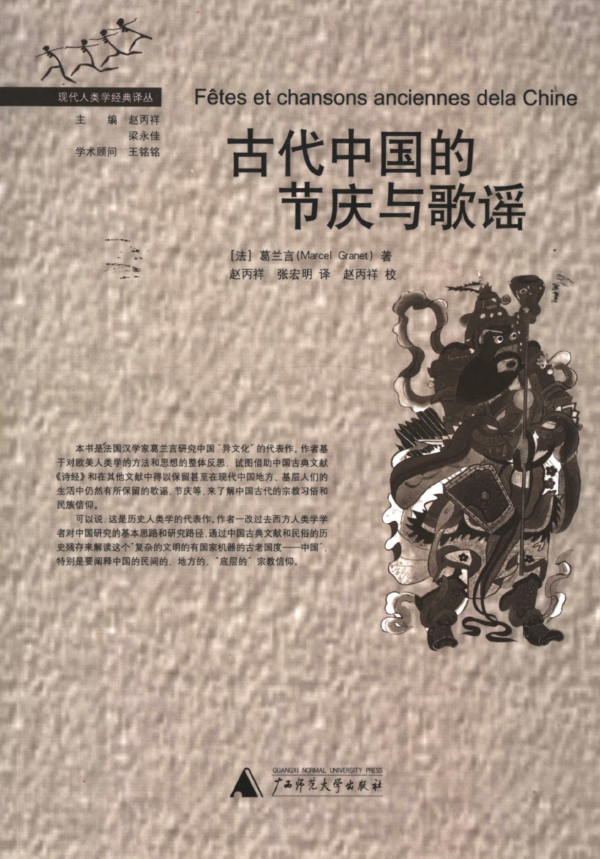
《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赵丙祥、张宏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2005年11月版
《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对于《诗经》解读的特别之处在于,相较于传统将诗经视作文学作品而对其中的诗歌进行语文解读和思想主旨的探析,葛兰言将《诗经》中的部分诗歌视作统一的内容整体,并以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从而尝试还原出先秦时代由中原先民的劳作分工、部落规则等方面所构成的社会形态——也正是前文所言七夕故事结局的雏形。
在本书的开始,葛兰言首先对较为主流的《诗经》中的诗歌主要出自学者之手这一传统观点进行了驳斥。传统观点的看法与诗歌的教育功能密切相关:“既然诗歌被用于教育的目的,它也被认为是为了这种目的创作出来”,因此人们相信后世作为教育之用的《诗经》出自诸侯国固定的宫廷学者之手。但葛兰言认为这一说法并不可信,他首先提出质疑:“为什么这些天才的阐释者(后世学者)会一再援引这些诗歌来满足他们当前的政治需要呢?他们原本可以自己创作的,他们并不是没有这种才能。”由这个问题展开探讨,他认为诗歌的田园主题以及它们表现出来的朴素风貌都表明了《诗经》中的歌谣是产生于乡村——因为在这些上古诗歌中,一个显著的事实是诗歌中不含任何的个人情感,所有的恋人都是一副面孔,都以同样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情感;这些诗歌表达了情感的主题,如约会、订婚等,而非直接抒发个人情感;诗歌中的场景也尽量地一成不变。因此,葛兰言断定这些诗歌绝非诗人个人的创作,其起源是非个人性的。而通过诗歌“简单直白的艺术手法、对称的形式、进行曲的步调以及似乎适于轮流对歌和需要借助手势补充语言表达的特点”,葛兰言认为《诗经》中的歌谣是在乡村的即兴对歌中产生的。
此外,葛兰言也注意到,《诗经》常常被后世之人用于道德教化,而如果其起源是个人性的情感抒发,是产生于对自然的朦胧诗性,那么诗歌之中理应不存在任何带有规约性质的力量,后人使用《诗经》来阐释道德教化功能也就没有权威的依据。结合《诗经》中的山川歌谣所描述的场面,葛兰言推断出,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方存在大规模的乡村集会的习俗——诗歌正是从中产生,进而由于这种集会具有某种仪式意义上的道德价值,从中产生的诗歌也就相应地具有对社会的规约作用,那么后世学者使用象征的方式来对诗歌进行道德教化方面的解释就是具有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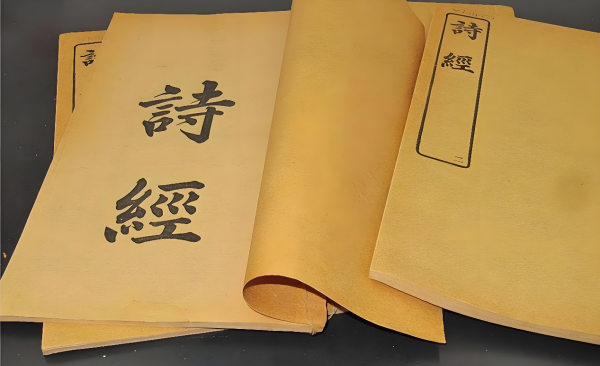
《诗经》
在揭示出诗歌被创作的来源之后,葛兰言进一步对其发现的仪式集会进行阐述。根据诗经中的诗歌多是情歌并且明显具有对歌的线索,他判断在集会中,年轻男女会分成两队,举行歌唱和舞蹈的竞赛,而爱情就是从中产生的;再根据诗歌中所描绘的景物,推断出集会的时间一般固定在春秋两季——在季节集会上,众多青年男女群聚于仪式地点,进行具有竞赛性质的轮流合唱,并以之相互挑战或表达爱情,确定彼此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些诗歌阐明了隐藏在经典正统背后的古老习俗,揭示出确实存在着乡村的季节节庆,正是由于人们对于节庆集会的崇敬态度才赋予了诗歌以神圣性,也正是这些节庆决定了中国农民生活和两性关系具有节奏性。
至此,这种古老的季节集会与七夕传说中牛郎织女有节奏的相聚(每隔一年)对应起来,其产生爱情的仪式也与七夕所传达的主题相一致;但传说故事中男方与女方的分离尚且没有得到解答,想要找到这种对应的关键证据,还需从先秦社会形态中的劳作分工体制入手。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葛兰言通过对郑国(河南)的春季节庆、鲁国(山东)春季节庆、陈国(河南)的节庆、王室的春季节庆进行研究,进一步完善了他的社会构想。葛兰言认为节庆之所以有固定的时间举行,与太阳周期、植物生长的周期以及农业的周期并不关联,却与婚姻的仪式之间存在着关联。“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春秋两季是举行婚礼的适当时期——或者,在春秋两季中间的时间,农民由一种生活方式转向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因此在婚姻仪式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农民的生活节律,或者说婚姻仪式本身是生活节律的一部分,而这种节律则是遵循男耕女织的劳作分工而产生的——在这种分工体系下,农民周期性地经历室内与室外、个人与集体的生产过程。而之所以如此严格地遵循生活节律,则是因为他们“按照自身生活的原则来想象自然的法则”,只要服从于这种生活节律,自然也就会以同样正常的方式运行——他们之所以坚信这种做法有效,是因为习俗在他们心中激起了信赖和尊敬之感,正如同古人会相信帝王的所作所为会引起天灾,先民也认为标志着共同体生活之情感时刻的季节节庆会对自然界施加影响,从而产生了对生活节律的严格规约。

男耕女织
从中国上古的社会形态说,当时人丁稀少,人们按照家族分散而居,不同家族的人平时很难谋面,而农业劳动要求男女两性分工,男耕女织,也就导致了男女两性之间的隔离,通常是聚少离多。对应这种情况,社会学家涂尔干曾提出,社会集团定期举行的集会会让人们进入“集体欢腾”状态,从而让社会在人们心中激起一种神圣感,社会的团结定期得到更新。葛兰言对于社会集会的阐述与此极为接近——“在这个时刻,社会生活突然进入了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中,由于它近乎奇迹般的强化作用,它激发那些成员对他们正在共同实行的行为所具有的效力产生了一种无可压制的信赖感。”而这无疑就是一种“集体欢腾”状态。但在此基础之上,葛兰言还进一步对中国古代社会在集体欢腾以外的分化状态作出了详细的阐释:他认为在集团分化的基础上,各个基础集团还进一步在内部严格实行性别分化,通过抑制基础集团内部的男女结合,保证“外婚制”的顺利实行——也就是说,集团间的婚姻以类似“人质交换”的方式展开,从而达到社会整体的和谐。
因此葛兰言对远古时代的中国社会形态的描述可以总结为以下规则:
一个乡的居民形成一个共同体,而共同体这种基本的集合形式根据劳动分工划分为两类基本集团:首要的分配原则是男女两性的劳动技术分工;另一个则是土地的地理分配。以这种方式,男女两性相互轮换,按照在季节交替节律的基础上形成的体系从事各自的工作。在全年中,隔离是规则,小集团的单调生活严格限制在日常的私人领域中。在这时也不存在所谓的“社会生活”,只有在全面集会的场合,共同体才能恢复以前的统一状态。
而在这种“集体欢腾”的状态中,爱情和诗歌同时产生。在即兴创作的诗歌主题中,铭刻着自然现象和人类惯行间实际存在的对应性,表明了自然规则和社会规则的统一,它们的权威也正由此而来。因而尽管在后世诗歌被以象征的方式不断曲解、变换寓意,其效力是不变的,原因就在于它们依然具有自然对应性。
顺着男女两性由于劳作方式而产生的分离,以及在竞赛中的对抗又结合的形式,葛兰言接着提出,其实中国人的时空观、阴阳观念都是从这种男女对歌的活动中幻化出来的。空间观念中的阴阳源自对歌时男女两队的站位;时间观念中有阴阳,是因为对歌中双方交替用相等的时段来唱。而“竞赛只是古老的社会结构的一个戏剧性表象,两性劳动分工才是社会结构中的原初性事实”。因此,葛兰言认为中国人的“阴阳”观念,最初实际上是源自男女分工的对立而来——“古代的劳动分工规则给中国人的思维提供了秩序原则”。
相对应的,在七夕故事中男女双方所对应的代表性劳动角色——牛郎织女(男耕女织)——被人为地分离,并且一年只能相见一次的模式也就呼之欲出了,这恰好与葛兰言所揭示出的社会形态相对应,展示出这个古老传说的社会原型。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