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0月20日,一场题为“诗歌与明清女性文化”的研讨会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行,这是英语学界关注明清女性文学和性别文化的研究者首度齐聚一堂,会议论文后来以专号的形式刊发于英文期刊《清史问题》(1992年第13期)。为专号撰写“导言”的汉学家费侠莉(Charlotte Furth)指出,这一主题的研究使大量明清上层妇女的文学作品“重见天日”(recovery),而这些古典诗词里的女性声音,为探索她们的智识和社交世界提供了新契机。同样在1990年,加拿大华裔学者方秀洁(Grace Fong)在一场北美宋代词学会议上报告了《论词的性别化——她的形象与口吻》一文(英文版1994年,中译文2003年),研究词如何从男性视角转移到女性声音,从此开启了她接下来数十年的研究明清女性之旅。在其为《跨越闺门:明清女性作家论》(英文版2010年;中译本2014年)编著所写的“绪论”中,方秀洁认为,以胡文楷(1901–1988)为代表的国内学者早已着手对古代妇女著作进行过系统整理,因此更确切地说,明清妇女著作在海外是经历了一个“重新发现”(rediscovery)的过程。
尽管两位学者的不同用词在内涵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对于方秀洁而言,重访明清妇女著作的意义显然远非仅限于为籍籍无名的才女作传、或是为这些女性的才学文章背书;她更关心的是女性文本生产的社会文化意蕴:“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对女性自己记录下的言行、思绪以及际遇等加以重视,才有可能解构那种过于简单化的成见,因而获得一种不同于既有观念的认识,揭示出中国社会与文化经纬的复杂多样。”(《跨越闺门》,页3)这种强调“重新发现”的思路集中体现在方氏的专著《卿本著者:明清女性的性别身份、能动主体和文学书写》(后简称《卿本著者》,英文版2008年;中译本2024年)。该书以士绅阶层的女性诗文集为主要分析材料,从节妇自传、妾妇创作、行旅书写、文学评论与编辑这四个主题来探讨文学书写之于明清女性的意义。作者将女性书写视为一种文化实践形式,力图阐明女性创作的运行机制,触及文本的社会与文化动力,回应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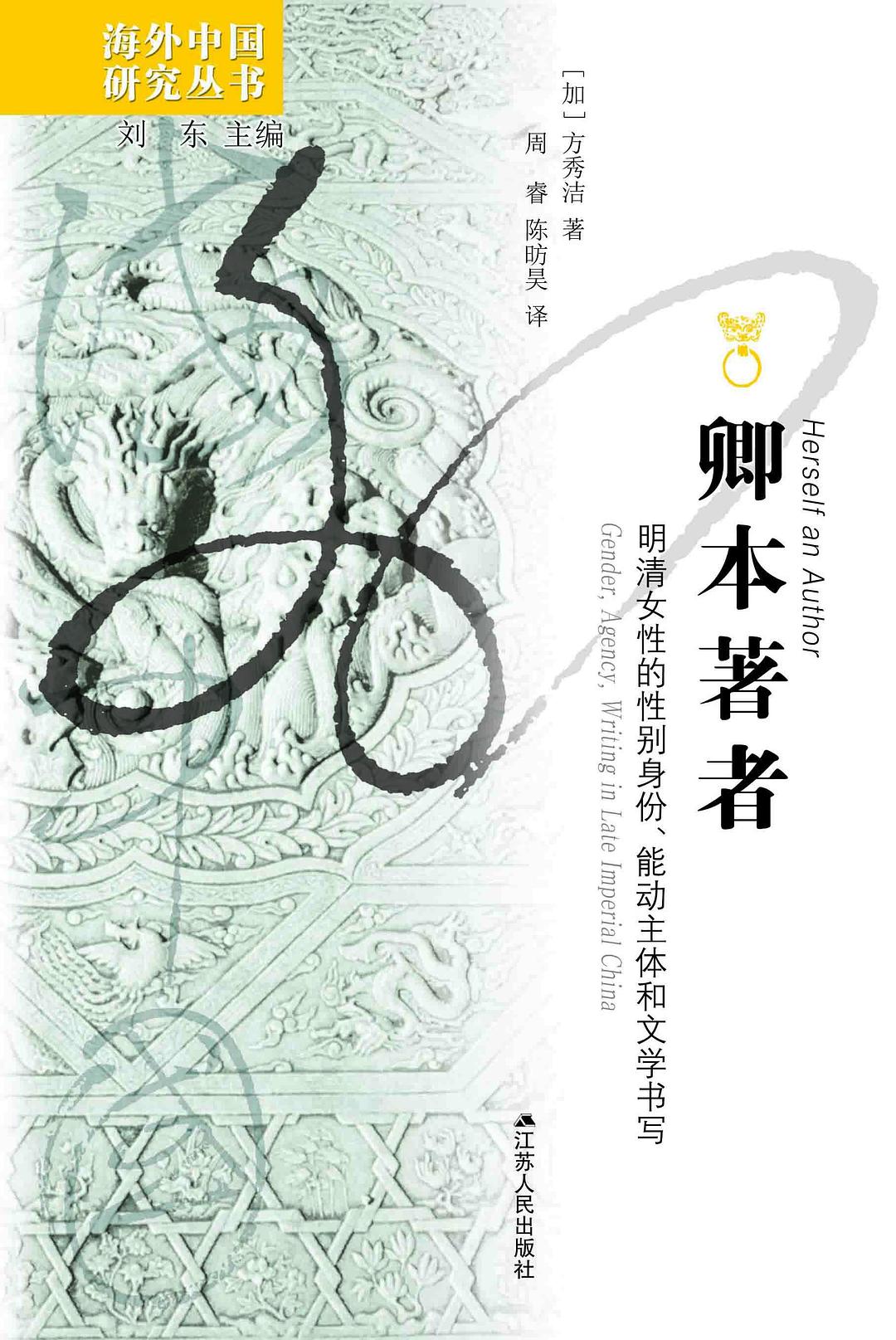
一、女性声音与能动主体
出现在《卿本著者》英文书名里的关键词“能动性”(agency)贯穿于全书对女性著者的文本分析。“能动性”观念(或表述为“自我性”/“个体性”/“主体性”)指的是自觉采取行动的能力与意愿,有助于阐释本书的中心议题——女性在规范化的性别秩序中对不同身份的自我表征/再现(self-representation)。这一议题将具有文化身份的“著者”(对应书名中的“author”)与女性著作中刻画的主人公“卿”/“自我”(对应书名中的“herself”)区分开来。前者强调的是女性的文本实践,后者强调的是女性角色的社会书写,这种区分将明清文学女性在儒家正统价值体系中“自我赋权”(self-empowerment)的努力与妥协同步展现出来。在讨论作者如何运用这一概念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其学术理路。
李小荣在《女性声音与主体:西方汉学研究明清女性诗歌的理论与方法》(2013年)一文里曾提到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指出历史的发展和文学的创新瓦解了对于“能动性”等同于消极反抗现有秩序的预设,“也许个人不能完全脱离意识形态和流行话语,但是语言的工具性和开放性,以及意识形态的多重性、复杂性,可以使个人有在各种主体之间选择、游移的可能性,并运作各种流行话语或解构、建构各种主体。”(《女性声音与主体》,页15)她指出明清女性文学为“能动性”理论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特别是考虑到儒家的性别秩序以及与之相关的女性关于著者权的焦虑。在此语境下探讨女性经验可以卓有成效地观察性别如何影响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进而促进文学和社会性别文化研究的新发现。
文学研究者雷麦伦(Maureen Robertson)在这方面有开创之功,其经典之作《改变主体:作者序与诗中的性别和自我书写》(Changing the Subject: Gender and Self-inscription in Authors’ Prefaces and ‘Shi’ Poetry, 1997)对女性诗人的自我再现分析,便区分了女性诗人主体身份的不同层次:一是存在主体,即文本之外的现实生活中的诗人;一是作者主体,即存在主体所扮演的著者角色,通常借序言发声;一是文本中的主体,即诗歌中构建的各种身份、形象。李小荣认为雷麦伦的文章回应了女性主义对主体政治的理论,具体阐明女性主体的错综复杂,并揭示女性通过文学改写与发明展现积极的创造力。
同在上世纪90年代,史学界对中国女性的研究也受到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启发,进而探索能动主体议题。代表性学者高彦颐(Dorothy Ko)在其先锋之作《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英文版1994年;中译本2004年)中借鉴人类学家Jane Monnig Atkinson的思路采用“双焦点”历史视角,将传统时期的女性视为“受害者”与“能动者”(agent)的结合,修正了五四话语视传统社会女性仅仅作为受害者的刻板印象,从儒家的理想模范、女性的实践活动、女性的自我认识这三重维度,生动地阐释女性著者与社会期待不断调适、磨合的历史。更值得注意的是,她引入了琼·斯科特(Joan Scott)影响深远的性别分析框架,重点剖析在17世纪明末清初语境下的“规范化概念”(来自儒家经典与教义)、“社会组织与机构”(诸如亲属体系或教育制度)和“主观认同”/“主体身份”(反映在女性著作里)之间的动态关系。
高彦颐认为,文学活动赋予明清之际士绅家庭的女性诗人超越其所在家族或所处时代的更为广阔空间的一种身份。这些女性所受的教育及其所抒发的感想更接近同时代的男性文人,而非道德范本中终日囿于内闱、操持家务的女性楷模。因此,这些女性的主体身份应当被置于她们堪与男性比肩的成就(例如文学创作)之中来理解,具体反映在她们与男性的文字交流、自身学习和传授书画技艺的意愿、鼓励志趣相同的女性友人增进艺术鉴赏能力等方面。尽管这些行为、志向、情感突破了传统的性别角色,与儒家正统学说的理想女性形象并不契合,但是因其表现出的谦卑以及对传统秩序的主动接纳和维护,因而受到儒家礼教的默许。
对于女性“主体身份”的研究之所以成为可能,得益于规模显著的女性诗文集的存世。正如曼素恩(Susan Mann)在其代表作《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英文版1997年;中译本2004年)提到的,将女性文本纳入分析范畴可以“观察在一个儒家规范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女性怎样陈说她们心目中的价值和意义。”(《缀珍录》,页4)在这种研究取径下,女性著者的能动主体议题成为理想的切入点。以《卿本著者》第二章“从边缘到中心:妾妇的文学使命”为例,作者聚焦浙江平湖显族之后陆烜之妾沈彩(1752年–?)的《春雨楼集》,深入挖掘沈彩的创作所投射的传统礼法意涵。妾妇在礼法上的边缘从属地位,使其“在情感表达上摆脱女子恭顺卑谦的正统束缚时也似比正室嫡妻要更为自如”(页83),使其主体身份的塑造更自由,因而也使其成为观察女性著者“能动性”的有利位置。
与要么算计大妇、要么遭嫉受害的刻板姬妾形象不同的是,《春雨楼集》中呈现的沈彩与夫君或是嫡妻的相处,大抵都是和睦而亲密的;陆烜的正室彭贞隐指点沈彩读书习字的画面,甚至让人联想到慈母课女的场景。当陆烜离家在外时,彭、沈二人则彼此陪伴。陆家的诗书氛围与情感纽带为沈彩的创作提供了宽松的环境,鼓励了其对“闺情体”诗歌的仿写。因而沈彩能够欣赏自我身体和才华,她的文学语言(如“春雨”暗喻房事)和意象(如“春山”暗喻酥胸)大胆地表现了男女情爱与身体诱惑,她还直言在“春日”里自己“欲写春词”,这些都成为其自我再现的生动体现,自然而然地将女性从被动的情色客体转变为以诗文主动表达自我的欲望主体。作为著者的沈彩还亲自参与个人文集的编辑、出版,也有诗歌评论传世。尽管从理论上看,她的性别和地位在礼法等级框架中居于不利的位置,但其在家庭成员的支持下赢得文学和艺术声誉的事实,又成为儒家性别秩序别具弹性的例证,呼应了高彦颐对于传统女性以创作突破传统性别角色的观察。
与沈彩相比,书中第三章《著写行旅:舟车途陌中的女子》论及的晚明重臣葛征奇(?–1645)的妾妇李因(1616–1685)对能动性的表达则隐晦得多。不同于身处闺阁的沈彩,李因随夫赴各地履职,游走于各种社交场域,因而得以在诗中着意刻画身为行旅者的经历与情感,“在男性与女性书写的旅行诗传统中协商与建构她的个体身份”(页142)。这些诗作在漂泊无定的旅途中塑造了一个有序、雅致的文化空间,也许是为了这种整体的秩序感不被破坏,李因并没有在诗文中直接留下途中遇兵乱而受伤的记录,而是借由黄宗羲(1610–1695)的传记使那段凶险的遭遇为人所知。在这个例子中,施展才情的行旅主体超脱于动荡的时局。虽然妾妇身份对于沈彩和李因的书写意义有所不同,但是两者都凭借诗歌主题和语言技巧塑造出与传统闺秀有所不同的女性主体身份;与此同时,像陆烜、黄宗羲这些男性文人的襄助,亦在不同程度上介入到妇女能动性的表达之中。
二、女性文化与性别意识
在能动性讨论的基础上,《卿本著者》一书拓展了学界对明清女性文化的讨论,特别是第四章《性别与阅读:女性诗歌批评中的范式、修辞和群体》所涉及的女性共同体议题。在本书面世之前,孙康宜、高彦颐、曼素恩、特别是魏爱莲已经在研究中触及女性的编辑活动,方秀洁进一步指出女性通过编辑和评论活动,能够将女性的话语空间“转化为一个彼此互联共通、表达更多特定女性指向文学观点的公共群体场域。”(页152)她分别考察了每位女性各自侧重的编辑策略:沈宜修(1590–1635)的《伊人思》主要考虑的是诗作的留存及其与女诗人的私人共情,诗作的批评鉴赏并不是重点;季娴(1614–1683)的《闺秀集》以教导爱女赏诗为名、行取舍评鉴之事,以谦逊之姿品论美学风格,引起读者对诗作文学价值的关注;王端淑(1621–约1680)的《名媛诗纬》提供不止诗作,还列入诗人们的生平传略,凸显道德基调;沈善宝(1808–1862)的《名媛诗话》集前述三部选集之大成,通过呈现女诗人之间的关系网络,构建女性文学共同体。通过解读以上四部女性诗选评注的形式与修辞,方秀洁呈现女性对“权威性、能动性、共同体性”的感知(页153),进而揭示明清文学生产中之于性别差异的渐增意识,以及女性在传统角色之外,以编纂者的身份集中呈现女性著者生平以及文学创作这些自我赋权的新尝试。
第四章对沈善宝的讨论最为深入。作者此前已对沈善宝的诗学实践有过考证与诠释(参见《书写自我、书写人生:沈善宝性别化自传/传记的书写实践》,英文版2000年;中译文2016年),可与本章参照阅读。书中关于女性共同体的思考来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启发,有助于理解诗词之于女性著者们跨越时空之隔建立联系之用,“身在其中的士绅精英阶层知书达理的闺秀才媛,能够超越血缘关系与社会体系的既有限制,而以其能文善诗之技来想象自己与她人归属于同一族类”(页181)。在这种连结松散的“话语场域”(discursive field)中,像“名媛”这类词汇即成为这个群体的共同称谓,由选集编者所定义的一种主体身份。
在作者的论证中,这种主体身份一方面具体表现在因年代不同而无缘与沈善宝结识的历史上的女性著者们。这些闺秀或以家族世系为基础,通过诗文创作与分享,彼此交游并成集群发展之势;或以妇德、才情为资本,以特定身份(如“闺塾师”)、特定主题(如“悼亡诗”)被集结呈现。另一方面,这一主体身份还体现在对其同时代女性的记录。这些记录中除了以上提及的家世、德行、才学这些构筑共同体的元素之外,还增加了情感纽带,“她们彼此守望相助,通过寄诗赠文来互通音信,维系联系”(页189)。在方秀洁看来,沈善宝录其亲朋挚友的这些条目颇有“日记风格”,具有“个人化”色彩,通过女性诗作中的个体经历表达彼此间的惺惺相惜之情。

清代年轻女子
在“个人的即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作者提出了“个人的即批判的(The personal is the critical)”的说法,以期更进一步理解沈善宝的“个人化”评论风格。不过,受限于《名媛诗话》的文本特征,这些条目呈现的“批判性”实际上相当有限。正如作者也提到的,沈善宝“以留存才媛文学遗产为务,而文学批评退居其次,故而其评注之语往往简略乃至通俗,且不吝溢美之辞”(页180–181)。这些与沈善宝同时期、以《名媛诗话》的编纂为动因而聚集在一起的、沈善宝同时期的女性著者,除了呈现给世人一张超越家庭和地域、流动开放的人际关系网络之外,还能揭示出女性文化的何种面向,这一点仍有待继续探索。
将这一女性共同体的研究置于学界对明清“女性文化”的讨论之中,又会出现另一个被反复讨论的议题:女性对自身性别的意识如何在儒家的父系制度下得到表达?一方面,以文学创作为主要表征的“女性文化”与儒家正统价值体系仍存在依附关系(Charlotte Furth, 1992),曼素恩以常州张门才女为例,更是明确指出文化传统给予女性创作的深厚土壤(《张门才女》,英文版2007年;中译本2015年)。另一方面,妇女的自我性别意识和独特性不该被忽视,高彦颐尤其谈到女性文化的独特价值正是建立在女性作为著者、编者、读者的共同爱好基础之上。在编纂诗选基础上构建的女性共同体为此提供了实证。
不过,在第四章的例子中,除了仅有一处论及沈善宝在与张门才女之一张䌌英的文学交流中直接“投射自我对性别不平等特有的愤懑之情”(页193)外,沈氏的性别意识更多地是通过文本形式、内容目次与编排架构、称谓用词等侧面得到反映(关于沈氏的其他表达不满于性别不公的诗作,见李小荣:《英雄主义的性别化:明清女性的〈满江红〉词》,英文版2005年;中译文2022年)。例如方秀洁认为沈善宝以“继室”而非“侧室”来指称顾太清(1799–约1876),并且对吴藻(1799–1862)婚嫁之事闭口不谈,实则是通过这种笔法表达出其对社会将女性污名化的无声抵制(页191)。受写作当时的资料所限,作者并未就沈善宝的文集刊印情况做更细致的分析,不过考虑到围绕其作品的未解之谜(《名媛诗话》在沈善宝离世十七年之后才得以付印,而且其《南归日记》未被刊印传世,笔者据此推测这与沈氏个人意愿或其族内男性的态度有关),才名远播、交游广泛的沈善宝对性别意识的表达,仍相当自觉地嵌入儒家正统的性别规范秩序中,而且其著作传播可能也主要仰赖于男性亲友的资助。即便如作者所说,重视诗才的沈善宝与强调德范的恽珠(1771–1833)有所区别,但就女性在父系制度下对性别角色的表达来看,两人的区别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诚如李小荣所言,“也许并没有一个独立在意识形态和话语之外的女性原生态”(《女性声音与主体》,页10),女性著者的创造力与男权社会的价值观始终处于这样一种动态平衡之中。
三、自我表征和文以铭世
方秀洁在自述学术心路时,曾提到自己搜集明清妇女著作是希望探讨历史上的女性如何在诗文中进行性别化的表征/再现(《致谢》页1)。在其早期的代表性研究中,她注意到沈善宝将时间序列作为其《鸿雪楼诗选初集》编排的依据,并且通过长篇散文体序言和在诗行间和文本内插入注释,有效地将这部诗集转变为自传性的写作。她认为沈氏以写作来“铭刻自我,通过各种方式向后世读者与诠释者暗示了写作中自我的具体体现——特别是,铭刻进文本中的性别化生活。”(《书写自我、书写人生》,中译文2016年,页233–234)这样的例子在女性诗文集中并不鲜见。
与由他人书写的传记相比,诗歌才是进入明清女性著者内心世界的更直接途径,是其自我表征/再现的主要载体。将诗歌作为“内心史”(interior history)的观点(参见宇文所安:《自我的完整映象——自传诗》,英文版1986年,中译文1996年)和将别集作为自传性书写的方法,为本书提供了整体的概念框架。第一章《诗中人生:甘立媃(1743–1819)之传/自传》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以编年次序清晰、凸显自传性维度的稀世文集《咏雪楼稿》为中心,结合甘立媃生平家世的其他文献,旨在理解其延续一生的自我再现。文集按照她的人生阶段被分成四卷,每个卷名生动地展现了其“妇功”实绩,呼应其人生不同阶段在家族中的身份地位:《绣余草》中在女红之外坚持练笔的天真少女,《馈余草》中享受婚姻之乐的贤内助,《未亡草》中独自抚育幼孩的孀妇,《就养草》中从子宦游、虚怀佐政的县令母亲。这种终其一生的写作实践,不断强化着她的自我意识,塑造着她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扮演。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甘立媃通过文字书写进入公共领域,辅佐儿子政务并得到百姓认可。她的“外交”角色得益于其作诗才华,这对其子的地方施政与声望至关重要。一方面,她对自身的性别限制有明确的认知,例如她用“再生缘”来隐晦表达建功立业的渴慕;另一方面,她更意识到文学创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己的夙愿,因此除了日常写作之外,还在自己六十、七十大寿之际赋长诗以自陈心迹,毫不讳言自己(特别是在守节期间)为家族所做的贡献。藉由一生的写作,甘立媃找到了在既有社会体系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文化渠道。
将自我的良苦用心置于家族等级秩序的这种表达策略,亦体现在第三章论及的邢慈静(生活于17世纪初)的作品中。这种叙述方式使其携幼扶柩还里、将亡夫归葬故乡的不易之举能够为后代所铭记,同时又不至于显出自我吹嘘之嫌。作者更进而推测,邢慈静或许还意图通过自己的行旅记录,代丈夫控诉因官场失意而英年早逝于异乡的不公现实。无论这是否是她的初衷,从结果来看,邢慈静的确如甘立媃一样,通过文学书写再现自我,既为自己发声,也为家庭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历史印记。
与第三章论及的晚明王凤娴相比,甘立媃的诗文刊印经过更意味深长。来自江南重镇的王凤娴,作品广泛见于前述若干女性诗选,然而其大部分诗文未能传世。据其弟称,她曾有意将数十年间有感而发的诗作付之一炬,后被其弟制止,而以《焚余草》为名刻集。无法得知王凤娴的“妇道无文”(页134)之说是真心认同,还是假意托词。不过,明清女性著者对于文集出版的态度的确是矛盾的,这与当时围绕着女性“才”“德”的争议密切相关。然而,这种争议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来自保守势力对女性才学的敌意。曼素恩指出,以章学诚(1738–1801)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其时代的女性在男性世界追名逐利的影响下日益变得功利,远离了妇道的应有之义。(《章学诚的〈妇学〉:中国女性文化史的开篇之作》,英文版1992年,中译文2021年)孙康宜同样认为,与其说章学诚是在批评其同时代的女性,不如说更主要的是针对当时因文学声望而表现张扬的男性文人,例如拥有众多女弟子的袁枚(1716–1797)。在章、袁二人之间、对“才”“德”持较为折衷态度的例子有编纂《国朝闺秀正始集》的恽珠,而其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比男性更“保守”。(参见孙康宜的论文“Ming-Qing Women Poets and the Notions of ‘Talent’ and ‘Morality’,” 1997)尽管难以衡量这一争议对于不同女性在创作上的影响,不过整体的舆论环境还是倾向于将“德”置于“才”之前的优先地位。
从作者的分析来看,与章学诚同时代的甘立媃的诗作并非上乘,表现为“烦言碎语、平白如话乃至朴实无华的风格彰明较著”(页65)。然而诗学艺术的平平无奇,并没有打消她将作品传之于世的念头。她曾在序言中自白,并未希望与古代才女相媲美,“她试图成为自己生活的著者,首要强调的是其文化价值而非文学价值”(页66)。与生活在晚明的王凤娴相比,甘立媃生活的乾嘉时期政治相对稳定,这种稳定正向的大环境或许促成了其诗稿的刊刻与传播。另外,她的自传叙述得以传世,或许还归功于其子金榜题名并被授予官职,“儿子就是她的‘成果’”(页55),这为她提供了安享晚年、醉心于文人雅好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基础。
尽管王凤娴也在孀居中独自将幼子拉扯成人,然而其子未曾在科举会试中及第,也无法为她提供更多的社会文化资源。从这个角度来看,“拥有一个立身于世的子嗣至关重要”(页64),有助于女性的个人声音为世所铭记。当然,如果对比作者在第二章对沈彩(与甘立媃生活于同时代)的论述,不难发现,子嗣尽孝与文集传世之间并非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集女诗人、书法家、鉴赏师与抄誊者于一身”的沈彩从未从母性的角度来构建自己的主体身份,究其原因,如果不是其确实未曾生育的情形(无据可考),便极有可能是身为庶母的尴尬的社会与情感处境,挤占了母性表达的现实空间。尽管如此,沈彩的文集在其生前更迅速地被刊印传播,阅者甚众,很可能还为家庭带来经济收益。由此来看,女性著者的自我铭刻方式,由时代、空间、地位、家人态度和资源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因而呈现出复杂多元的面貌,也值得更进一步挖掘。
结语
在上世纪90年代,当明清女性著作研究在海外起步时,大多数文本并未公开,即便是与此相关的两部标志性论文集(即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97和Chinese Women in the Imperial Past: New Perspectives, 1999),对女性文本的利用仍相当有限。为了使更多同行能更便利地接触到大批数量可观但馆藏分散的文本,发掘其中独特的女性声音,从2003年起,方秀洁依托麦吉尔大学与哈佛燕京图书馆建设“明清妇女著作”数据库。在此后的二十年间,共将431部来自多家图书馆的女性诗文集数位化并全球公开,目前仍在持续更新。此外,方秀洁和伊维德(Wilt L. Idema)合编有《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妇女著述汇刊》(2009年),在推动明清妇女著作的利用方面,走在学界前列。《卿本著者》可谓是这项国际合作数字工程的首部研究成果,将以高彦颐和曼素恩为代表的学者对中国古代女性历史的修正式(revisionist)探索和重写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本书不仅讲述诸位女性著者的经历,还探究她们创作实践的方式,更试图寻求“讲述她们的方法”(页4)。通过结合地方志、家族文献等女性文集之外的史料,方秀洁对这些女性著者“能动性”的诠释,兼顾了文学修辞和历史语境的双重考量。她从文化实践的角度,探讨女性如何凭借自我铭刻的文学书写来展现主体身份与性别意识。除了将西方文艺理论创造性地运用到对明清妇女著作的分析之外,本书的英文版还首次翻译了数量可观的女性诗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华古典诗词文化在英文世界的传播。
自从《卿本著者》的英文版问世以来,海外汉学界对明清女性书写文化的研究持续深化,将女性著者的文化实践落实到更为详细的专题讨论中,如李小荣、王燕宁、杨彬彬等分别从“闺”阁诗歌、游记、传记等角度考察女性的能动主体。最新的集体成果体现在去年以《对著者身份与能动主体的再思考:明清时期的女子与性别》(Rethinking Authorship and Agency: Women and Gen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为主题发表于《中国文学文化》(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的一期特刊文章,将对性别书写的文化考察拓展到更为具体的时空维度,回应此前研究备受关注的才学与德范、挑战与妥协、闺门的内与外等经典议题。
需要指出的是,将女性诗文集视为自传性文本的研究方法,呈现的主要仍是女性著者或其文集资助者所刻意筛选、编辑、拼接的声音与形象,与作为“存在主体”的著者本人并非完全一致。女性在现实世界里谈及的有关性别、阶层、时局等方面的思想见闻,甚至一些情感表述,都有可能在文集刊印的过程中被改写、被过滤以致湮灭不闻。为了应对女性传世文本的这种局限性,将文本解析与历史语境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势在必行的研究趋势。随着史料来源的多元化,加之现代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女性个体的生命历程及其交游网络将得到更为系统、直观的呈现。有理由相信,在个案研究不断深入的基础上,对于具有代表性的女性文本、生活、思想等多方面的解读也将推陈出新,这或许将更好地引领今人通往明清女性著者的精神世界。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