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很多中文世界读者对刘绍华或许并不陌生。她是一位医疗人类学者,是《我的凉山兄弟》的作者,她在职业生涯中见识过不少“恐怖世面”,“跑过华航空难新闻,上过保钓号采访渔船,在柬埔寨等贫穷国度做过国际发展,在尼泊尔陷入武装暴动烽火之中,深入四川山区的毒品与艾滋病重灾区,拜访过中国各地的艰苦麻风村。”
2018年7月,刘绍华的母亲和她自己接连确认罹患“世纪之症”,母亲被诊断为阿尔兹海默症初期,刘绍华则确诊淋巴癌。五年后,女儿积极接受癌症治疗已然好转,而母亲则进入了疾病的中后期阶段,随着记忆包袱不断破洞,母亲慢慢走向了释然和放松,甚至已经忘却了女儿患癌的事情。刘绍华说,“我们生命共同下坠的交会已然过渡。”
母女共病让整个家庭备受打击、陷入混乱,一开始,生病的人不好过,没生病的人也不好过;但是,在之后的数年间,“各种没想过的生命经验,正面的、负面的、坚固的、新生的、美妙的、创造的,也都一一发生;没生病的人很惊奇,生病的人更惊奇。”刘绍华在《病非如此》一书中写到,“生病与康复都是一趟旅程,只有走过才知道风景微妙,不管是否喜欢。”
《病非如此》展现了她作为癌症病人、作为认知症患者的女儿、作为医疗人类学者、作为疫情之下的中国台湾地区社会观察者等多重视角,在她的患病与疗愈叙事中,我们能够看到病人如何接受身体与生活的剧变、一个家庭如何应对疾病的冲击和震荡、医护群体如何接住下坠之人,以及一个社会可以如何真正地履行照护的职责。

刘绍华在本书最后一章的结尾部分写到:“我和母亲都与自己的某种面向和记忆告别。我们仿佛都回到某个生活的原点,然后又从原点出发,带着新的心情和姿态,与自己和他人互动。我们都因生病而经历了生命的减法。若换一个角度看‘失去’、‘去芜存菁’后,留下来的是对我们真正重要的或我们珍惜的。由此再往前走的生命之途,也许并非生命的减法,而是在观点和认知改变后,重新体会生命的加法过程。”
《认识病人的身心世界》(节选)
撰文 | 刘绍华
生病或老化的身体,很多感受一言难尽,因为病人可能正困惑于不明所以的处境,也可能难以启齿内在的忧心。病人在跨越身心的边界时,能靠什么摆渡以顺利超越现况、朝向安顿之境?我想,除了良好的治疗,以及病人自己的身心探索与活在当下的修行功夫外,亲友的同理心、照护和言行反应,也是下坠之人能否被接住、顺利摆渡过关的重要因素。
当我陷入化疗副作用和孤立无聊导致的身心变化时,母亲也正陷入脑部退化的风暴之中。半年的治疗期间,医嘱尽量回避亲友探视,以预防感染。母亲虽常跟我通电话,但只能等待我的白细胞数回升且哥有空时再带她来看我。虽然我们对各自病程的认识和投降的时间点不同,却同样经历过身心下坠的慌张。亲友面对我们的改变而有的困惑和不适反应,也颇为相似。
我接受治疗约三个月后,母亲从担心和挂念我,变成只有挂念,到主要剩下为何我都不回家的疑问。她逐渐忘记我生病了。我偶然发现母亲遗忘此事,感到难得的欣慰,从此在她面前绝口不提。
我以为,遗忘不好的事就等于放下。但是,仍有清晰逻辑认知的母亲,不见得这么想。
有回聊天,母亲提到一些她记不清楚的不愉快往事,我说:“这些事忘记了,不就轻松了吗?就不用再想了啊。”
母亲偏头瞅我:“怎么会轻松?”我又问:“那是什么感觉呢?”
母亲低下头,似乎认真用力地在思索:“觉得很……懊恼,想不起来,很懊恼。”母亲用加强语气说了“懊恼”两次。
我有点讶异,这是非口语的正式用词,母亲的表达能力仍然非常精准。
母亲和我的对话让我明白,没有完全遗忘的记忆,仍是记忆。记忆破碎的状况勾引出自我认同的焦虑与懊恼,哪怕是不愉快的记忆,都不想失去。母亲想要拾回的,不一定是记忆本身,更是记忆的能力。

母亲经常清晰具体地描述自己的脑雾状态,她能认知并表达细微的变化。有一天,我牵着母亲的手散步,她突然问我:“你有没有觉得我走路摇摇晃晃?”
其实,母亲走路并没有摇晃,但那是她身体内在的真实感受。我在治疗后期,偶尔也有那种身体内在非常脆弱,像是随时想坐下的感觉,但是外人完全看不出来,甚至可能以为是病人的幻想。
那不是错觉,是真实的感受,病人正在辨识体内的信息,并努力稳住自己。
母亲经历的病识感,是种觉察自己正在下坠的失控感受,尽管速度不一定很快,方向却很明确。我感同身受。
治疗期间,我的病识感也很明显。在一般的社会认知里,化疗就像是把“毒药”打进身体里,癌细胞杀死了,无数的好细胞也阵亡牺牲,化疗就是一种必要之恶。我的病识感,主要源自化疗的副作用,而非已受药物控制的疾病本身带来的伤害,所以,我相信自己渡过化疗的难关后将得以康复。然而,尽管有此信心,我都免不了陷入低潮。快速老化愈逼近,失智症病况愈明显的母亲又如何能有信心,如何能安置自己的不安?
***
重症罩顶,不论治疗与康复,或祈求改善,都是一段漫长之旅,充满了酸苦、喜乐、不安与盼望。经常,病人处于莫名未知的跌宕起伏之中。身体情况退步时,心情也可能坠落得很快;身体情况稍好时,心情也可能宛如拨云见日般瞬间开朗。然而,通常旁人理解疾病与病人的脚步,少见能同步跟上。
常见的是,亲友可能在不明所以、不知所措或无话可说时,单调重复地要病人“勇敢”“振作”“加油”“开心点”“好起来”“不会有事的”。仿佛表现“正常”“开心”的关键在于主观意识,宛如病人的忧心与身体感受只是不必要的错觉,宛若回避讨论病人的恐惧,真实的危机就可以被压抑褪去。
常常,这样的言辞尽管善意,却多源于误解,成为不经意的伤害,甚至可能让病人产生不被理解的被遗弃感。此时,如果病人无法找到安顿自己身心的方法,不利的外在环境,以及缺乏理解及同理心的旁人言行,可能会加重病人的下坠感。
病人最需要的并不是勇气,而是活在当下的领悟与示弱的美德。向生命示弱、向身体的需求示弱、向愿意倾听协助的照护者示弱,才能放下忧虑负担,安顿虚弱的身心,集外界所有协助之力、之气于一身以感受支持,而不是刻意表现坚强。
愿意接受治疗就是一捧求生的勇气了,无须更多的宣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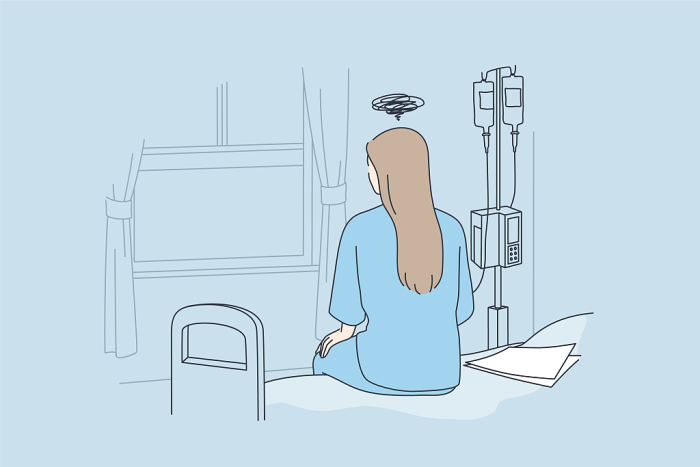
治疗开始后的我,偶尔在亲友的眼里可能判若两人,我想,很多重症病人或失智症初期患者都可能让身旁亲友有此感觉。得了重病,病人的认知、眼光、身体感、与周遭的关系,可能会被迫快速改变,直觉性地自救于恐惧和危机之中,想弄清楚为何?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该怎么办?言行举止习惯等日常生活选择,也可能随着这些自问自答而不停调整。
对病人而言,这一切安顿自己身心的改变,可能是立刻发生,毫不犹豫;也可能是在慌乱中摸索,跌跌撞撞,反复尝试,因而显得举棋不定。无论如何,专注于自身生命与生活的变动,让病人的内在调节启动得很快,表面上看还是同一个人,实际上却可能已进入准备脱胎换骨的正负状态。然而,旁人对于病人的认识想象,经常仍留在原地。
治疗期间,和许多病人的经验一样,我也会面对家人的不理解,这常令我想起三十二年前母亲化疗返家时的那一天。
那时的我无知且不成熟,不晓得如何应对生病的母亲,虽听闻化疗很伤元气,对于迎接母亲返家后的照护,却全然不知所措。犹记得,虚弱的母亲进门后,不发一语,不如我预期那样直接进房休息,而是坚持拖地,我要她不要拖了,表示由我来拖,她也决绝地不予理会。
几十年来,我一直不解母亲为何化疗后返家就在擦地板,但她固执生气的样子,始终印在我的记忆中。直到我自己接受治疗时,才终于似乎突然了解母亲了。
我住院时某天,朋友带着一大束花前来探望,医师看见了花,也见到友人没戴口罩围在床边,立刻叮嘱将花移走,还要我在床前贴上“禁止探病”的告示。我后来也在其他病人的医师口中听到类似嘱咐。因为多数人对于化疗中的病人,尤其是正在接受全身性化疗的病人处境缺乏认识,可能在不经意中造成预期之外的伤害。
化疗药物正发挥效果之时,也是副作用让病人的免疫力降到谷底之际。这时,寻常的细菌病毒都可能让病人发烧,从而影响治疗进度,甚至出现复杂的并发症。虽说现代人身边几乎都有亲友罹癌并完成治疗,但这一点常识仍相当不普及。
开始化疗前,新病人都得上卫教课,我就看了两支片子并听取讲解,完成后还得签名确认,可见其慎重。每回治疗后,医护都再三叮咛:勿碰触动物、植物;餐餐刷牙;接触口腔的任何器具都要开水消毒,尤其是牙刷;避免生食,只吃可削皮的水果,容易带菌和引起过敏的虾蟹海鲜等一律回避;出门一定要戴上口罩,远离人群;散步尽量挑选人烟稀少的空旷之处等。

刘绍华 著
望mountain·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7
这些叮咛都是良言苦口,看似简单,但要日日认真执行大半年,其实并没那么容易,需要一定的耐心和纪律。我认识一位病友,觉得餐餐烫牙刷太麻烦,就准备了大把的新牙刷,两三天更换一只。尽管如此,她的舌头还是长满了霉菌,必须治疗。病菌繁殖快速,免疫力低下的病人,连如此寻常的病菌都可能招架不住。
因为这些叮咛,第一次出院返家后,为了尽量避免过敏原和维持环境清洁,我就把绿油油的室内植物移到阳台或送走了,也把我搜集多年却可能藏有尘螨的布玩偶们送走了,在冷清清的环境中度过了六个月。医生知道我的职业,还叮嘱我不要翻阅图书馆或档案室里尘封多年的书籍或档案,因为那里面的尘螨也可能让免疫力正低下的我有“致命风险”。
然而,如此小心谨慎虽然确实让我在治疗期间未曾出现高烧或不必要的感染,免于不少化疗中常见的小警报,让我的治疗一路都很顺利,但是,窝居时没有喜欢的植物陪伴并不好受。这个经验,让康复后的我很希望了解什么样的植物可能适合陪伴病人。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病非如此》第二章,经出版社授权发布,标题为编者自拟,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