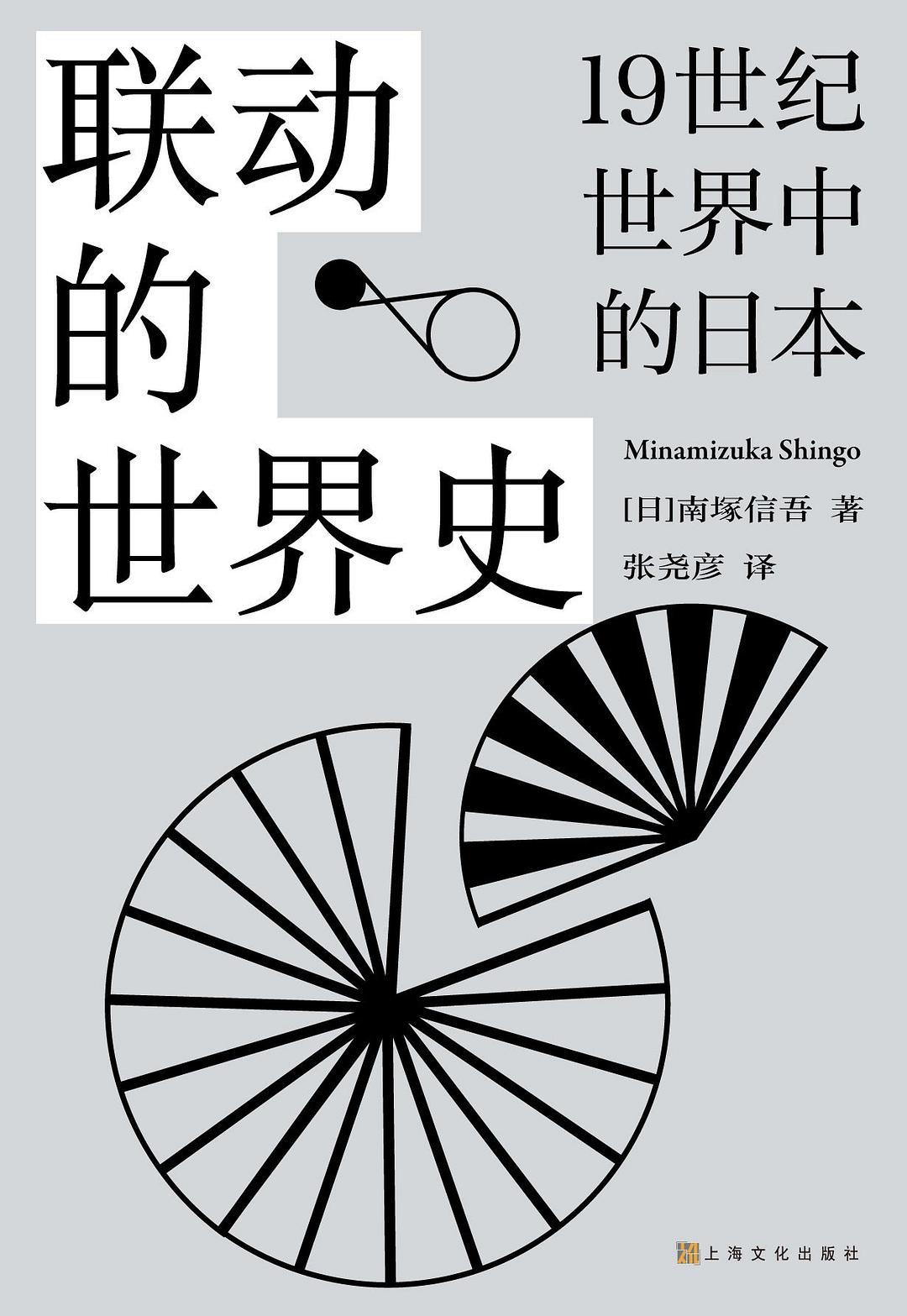
《联动的世界史:19世纪世界中的日本》,[日] 南塚信吾著,张尧彦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224页,58.00元
日本的历史研究,历来分三块,即国史(日本史)、东洋史和西洋史。这种学术“传统”虽说是其来有自,细究起来却是近代的产物。从幕末到明治初期,一些志在“入欧”的日本学者通过西人用英文撰写的万国史教本,来理解西方和日本所处的亚洲的历史,形成了日人最初的泰西史和东洋史的学术框架。在“近代日本的黎明期”刊行的若干种历史读本,如《泰西史略》(手冢律藏著)和《万国新史》(箕作麟祥著)等,均为这类著作。
回过头来看,既移植西人的历史叙事,便意味着接受西方史观,欧洲中心主义自不待言,连种族论也一并拿来,的确是万国史时代日人泰西史的局限。严格说来,就连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其《文明论概略》中所呈现的世界观,那种所谓“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本质主义思维,也未溢出那种认知框架。对此,明治后期的东洋历史学者,开始意识到在世界史的观念框架下重新审视历史的必要性:如历史学者、曾受聘于京师大学堂的坂本健一质疑以往的万国史“地域大抵限于泰西,存在雅利安以外之民非人、欧美以外之地非国的观念”,另一位史学家高桑驹吉则认为,“完整的世界史应始于东西两洋并叙”。
至此,万国史全面升级。1900年以后面世的万国史读本,更准确地把握了欧亚大陆和非洲的历史,且在展开东亚论述时会结合日本的历史,日人对世界的认知进入世界史时代。上述两位史学家,也都在那个时期推出自己的史学著作:1901年,坂本健一在博文馆出版两卷本《世界史》;高桑驹吉则先后于东亚书院和金刺芳流堂出版了两种世界史读本,《袖珍世界史要》(1903年)和《最新世界历史》(1910年)。这些出版物,均代表了“黎明期”之后日人进阶版的世界认知水准,一时纸贵洛阳。
明治末年,出于日俄战争后,大陆政策拓展的战略需求,日本正式在国立高等教育机构设立东洋史学专业(京都帝国大学于1907年,东京帝国大学于1910年),东洋史研究步入行政轨道,遂有后来以桑原骘藏、内藤湖南等学术大咖为代表的“京都学派”的中兴。而东洋史的学术繁荣,客观上又促进了日本的西洋史和世界史研究,尽管世界史始终未能在日本彻底“复权”——被冠以“世界史”的出版物远不如“西洋史”更流行,遑论西洋哲学史、西洋艺术史、西洋建筑史等子部类。
不过,流行不等于研究,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学术的普及。事实上,泰半由于孤悬海上、偏安一隅的地理环境所致,日人对外部世界有种近乎本能的渴求,其强烈程度远超其他国族,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情报控”:从历史文化、政经社会到世道人心,关于异域,不存在“冗余”信息,只有未悉的新知。就世界史的普及度及其在精英阶层的认知浓度而言,日本是相当高的。这既与国民的识字率和教育程度有关,也与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特别是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有关——日本的近代,是一个牵涉面既广且深的问题,当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史。
在一些大学主办的历史悠久的市民公开讲座中,世界史一向是最受欢迎的内容之一。B站上有一档教程,原本是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本科生通识课,由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羽田正等五位教授轮流主讲世界史,总题目叫做“关于‘世界史’的世界史”。“越境”上网公开后,竟粉丝如云,俨然成了网红课。上世纪七十年代,大报《每日新闻》社利用其海量的新闻摄影档案,出版了一套卷帙浩繁、脍炙人口的图片当代史——《一亿人的昭和史》。除了主系列的皇皇十五卷,还包括两个子系列:一是《世界史之中的“一亿人的昭和史”》(六卷),二是《日本殖民地史》(四卷)。可以说,两个子系列都是外部视角:把一部日本现代史置于世界史的容器中,在国际大背景中凸显了日本现代史的某些关键性节点,多了一个维度,从而使历史看上去更立体、更丰满。
如前者,六卷本的书名本身,便勾勒出日本现代史与东亚地缘政治和世界史的关联:《俄罗斯革命与大正民主(大正元年-15年)》(一)、《从世界大恐慌到满洲事变(昭和元年-7年)》(二)、《二·二六事件和第三帝国(昭和8年-11年)》(三)、《从日中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昭和12年-15年)》(四)、《太平洋战争和纳粹的毁灭(昭和16年-20年)》(五)、《东西方对立与朝鲜战争(昭和20年-27年)》(六)。这套图片史,一直是我的爱读本。笔者的另一种案头工具书,是《日本史&世界史年表》(NHK出版)。虽说是历史年表,但体例颇复杂:每页从上到下分成两部分:日本的动静和世界的动向;各部分又分别由大事记、历史事件小专栏、历史人物关系图、地图和历史照片等内容构成,重视觉性。直观地呈现了幕末、维新以降的百年史,可按时间线查阅,极其方便。以我长年浸淫日本历史类出版物的直觉来说,在日本史叙事中有机地勾连世界史,打通“国内小气候”和“国际大气候”之间的区隔,在贯通、流动的气场中复盘历史,确实是近年来日本学术界着力的方向。
这本《联动的世界史:19世纪世界中的日本》(以下简称“世界史”),正代表了这种学术努力。此书的日文版,2018年由岩波书店出版。作为“日本之中的世界史”书系(全七卷)的起头卷,聚焦从幕末到明治维新后的时段(1840-1910),尝试发现日本与世界的“联动”,进而从中复原新兴明治国家成立的历史轨迹。
当然,这种尝试并非基于新发现的史料,而是基于一种新的历史叙事。英国史学家E. H. 卡尔说:“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不在于记录,而在于评价。因为,假如历史学家不评价,他又如何知道哪些东西值得记录呢?”评价意味着建构一种历史叙事,而新的历史叙事则须建基于某种价值框架之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克罗齐宣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克罗齐的思想深刻影响了英国思想家柯林武德。后者在其史学名著《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一书中说,历史所关注的既不是“过去本身”,也不是“历史学家对过去的思考本身”,而是“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并不是死气沉沉的过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仍旧活跃于现实生活中的过去”。反过来说,假如历史学家不能理解一个过去行为背后所隐藏的思想,那么这个过去的行为就是无生命的,对历史学家来说是无意义的。据此,柯林武德断言,“一切历史是思想史”,从而把克罗齐的论断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历史就是一个对这种思想的历史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以自己的观念重新加以组织的过程。”
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核心是“关系”,所谓历史的思想史意义,是从过去和历史学家对过去的思考的关系中浮现的,而关系同样也是这本“世界史”的重中之重。不同的是,柯林武德的关系中有鲜明的主体性(历史学家);可同样的主体性,在“世界史”的关系中,似乎退到历史的后台。但退到后台,不等于退场,有能力将各路错综纷繁的关系依一定的逻辑线索加以串联、编织、重构,且不以伪史来欺世、玩世者,只有历史祭司(史学家)——历史研究的确是一种志业。
“关系”也是黄仁宇大历史观的关键词之一。他有本文集,书名就叫《关系千万重》,其中写道:“我所谓历史,属于人类及其生活之领域能为逻辑所操纵,亦即当中有各种关系之存在。”换言之,不能脱离关系谈历史,能为逻辑所阐释和驱动的关系,才是构筑历史的砖木。在这种“关系史观”的视域中,连日本史和世界史的边界都变得模糊、暧昧起来,很大程度上打通了从国别史、区域史到全球史的藩篱。因此,历史学者、同为“日本之中的世界史”丛书作者之一的小谷汪之认为:
任何社会、民族、国家的历史都不是脱离外部事物完全从内部发展而来的,而是通过与其他社会、民族和国家之间缔结各种关系,在这些关系的综合作用下发展起来的。将社会、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视为外在因素,只从各个社会、民族、国家的内在因素来探讨历史发展的方法,是支持日本史和世界史的基础。
这本“世界史”就其文本所描绘的时段而言,大致相当于日本帝国前期史。它并不以一国一地为中心,而是力求在十九世纪的国际关系中发现“日本的世界史,世界史中的日本”,旨在凸显一部“去中心化的世界史”。在这部以“关系”为经纬编织的世界史中,不时会出现“潮流”“联动”“本土化”等关键词,这正是此书之不同于通常世界史叙事的特性,也是其独到的历史分析方法:
世界各地在相互关联的过程中,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互动”,使世界历史的主导“潮流”不断蔓延,并按照当地的方式“本土化”。不同地区的历史也因此而“联动”起来。
这些主导潮流包括军事制度、学术制度、国家和边界的概念、外交和条约的概念、宪法理念(包括选举和议会制度)、民族和民族主义、殖民地分割理论和殖民地统治方式,等等。当然,这并不是全部。这些潮流传到各个地区,为了适应当地的条件接受了“本土化”,同时“本土化”的还有“潮流”连带的各种问题。
不过,这种世界观迟早会面对一种道德诘难:所谓“潮流”的“本土化”,难道不意味着“欧洲模式”的一方通行?对此,作者早有预案,并在逻辑上予以回应:
仔细想想,这种看似欧洲式的“潮流”,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对亚洲动向的一种反应,或者是以牺牲亚洲为代价产生的。例如,工业革命是在亚洲纺织品的威胁下发生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在亚洲局势持续紧张,欧洲趋于和平的背景下奠定了基础。……其中一部分(潮流)即便不是从亚洲反向输入,也是在与亚洲的接触过程中于欧洲形成、转化和加工而成的。可以认为,那些看似欧洲的固有的“潮流”,是在整个世界的“联动”中产生的。
这里,“联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表述:不同区域之间的相互诱导、不同关系之间的交互作用,靠的是联动。不仅地区和国家间外交政策的执行,需依赖联动,“外交与内政一直是联动的。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外交上的问题并非仅仅通过与外国的交涉就能完成。国内党派之间在外交方针上的分歧必然会影响到内政”。
除此之外,还有所谓“橡胶气球”理论:“就国际关系而言,整个世界就像一个‘橡胶气球’,如果某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那么其他地区的紧张就得以缓和,而某个地区局势缓和,那么就会有另外的地区局势紧张。”这原本是历史学家江口朴郎在战后初期提出的观点,在本书中被引申为帝国主义论,用来形容世界不同地域之间的“有机”互动;在对列强角力、争夺殖民地的国际权力场的评价中,则导入了民众运动的维度——也是一种“关系”。
对中国读者来说,这种分析方法确实耳目一新。如对幕末开国的解读,日本史教科书上的公式说法,是以佩里“黑船”来航为标志的美国炮舰外交(所谓“外压”)的结果。可“世界史”却告诉我们,因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欧洲局势空前紧张,列强无暇东顾,客观上造成了东亚地区的缓和。幕府统治者审时度势,充分认识到日本的弱国处境,慎重做出了开国的抉择。但随后即确立了与诸列强“等距离外交”的战略,变“消极开国”为“积极开国”,同时顺应外交、通商、条约等世界史的“潮流”,并推动其“本土化”,进而为我所用……这种分析框架从根儿上颠覆了传统的所谓“冲击-反应”认知模式,显然更契合日本近代的射程,似更富于解释力。
最后,请允许我扯两句题外话——关于“世界史”的阅读感受。这本书的篇幅虽然不大,信息密度却极高,且由于打破了日本史和世界史的边界,对读者的史学素养和逻辑训练有一定的要求。但惟其如此,阅读此书是一个持续烧脑的旅程。因知识点过度浓密,且不同部分之间链接频密,似乎不大支持“一目十行”式的速读。如能每天读上几页到十几页,边读边思考,一路读下来且不放弃的话,那感觉还是相当美妙的:如乘游轮浮于海,你站在甲板上远眺风景,时而确认手中的海图。视界中的海岸线、岛屿和海图相互提示,游轮仿佛沿着世界史的动线航行。而游轮尾部拖曳出的长长的水线,宛若近代日本的发展轨迹。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