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从100年前一场演讲说起。1923年2月,北京大学张君劢教授在清华大学做了一场题为《人生观》的演讲,提出了科学与人生观的复调叙事,强调科学并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他指出,如果我们仅仅追求科学技术,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科学为论理(逻辑)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是综合的;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与自由意志相关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则起于人格的单一性。
我们今天在讨论医学的时候也会发现,医学就像张君劢教授讲的,不光关乎科学技术,也关乎我们的人性或者说人生观。医学是人学,是人文牵引的科学,人性滋养的技术。医学的价值关切是人生观、价值观的具体化,包涵生死观、苦难观、疾苦观、健康观、救疗观。我最近新出的《反弹琵琶:医学的现代性批判》一书回答了关于医学的哲学悖论,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医生做得越多,老百姓的抱怨也越多。这背后包含了医学的一个隐喻,医学是双头鹰、双翅鸟,而没有人文滋养的医学科学是单翅鸟,没有人性温度的医疗技术是无花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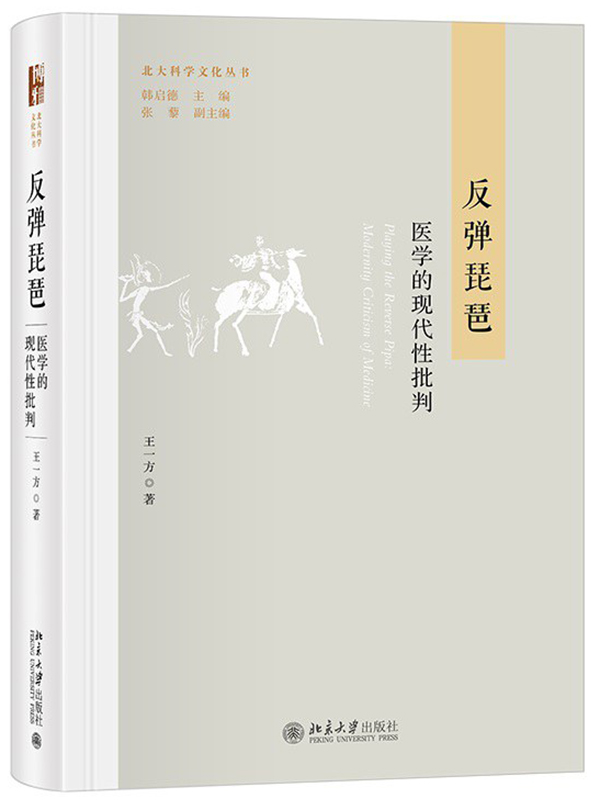
《反弹琵琶:医学的现代性批判》书封
美国医学伦理学者佩里格雷诺(Edmund D. Pellegrino)曾经有个经典的论述,医学是科学中最人文,人文中最科学的学问。医学关涉最基本的人类价值,即利他和纯粹。医学的一端是科学和技术,另一端是苦难中的人类需求。医学决策联系技术和道德命题,因此,医学既要客观,又要充满同情。他的结论是,是否学医取决于是否具有一种品质,那就是对于人类痛苦不可遏制的敏感。
在西方的STM(Science,Technology and Medicine,科学、技术和医学)分类体系中,医学和科学技术是并列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这是因为科学和技术追求的是有知、有理(客观、实验、实证、还原)、有用、有效、有利(效益最大化),而医学有着更丰富的价值半径,除了上述几点之外,还要有德、有情、有根、有灵,其中包含了科学性、人文性、社会性的统一,追求的是生命价值的最大化。
100多年前逝世的特鲁多医生的墓碑上刻着三句话:有时,去治愈;常常,去缓解;总是,去抚慰(to cure sometimes;to relieve often;to comfort always)。他通过自己医生行医的体验告诉我们的是,通过诊断、治疗使得躯体的疾病痊愈的概率是不大的,医生更多的时候是要去安慰、疏解患者心理上的沮丧和忧伤,这是无法用科学去证明的,往往是一种心灵的感应。作为医生要明白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医生无法包治百病,但可以情暖百家,抚慰百心,安顿百魂。现在我们对医学的理解越来越立体和全面,一个好医生应该从身、心、社、灵四个方面来面对患者,而不仅仅是找到一种药或者做一个手术。
从医学哲学的角度来看待生命、健康和疾病,背后有很多大概率和小概率的问题。哪一个生命、健康、疾病,我的还是我们的,个体的还是集体的,个性的还是公共的,是我们要思辨的问题。从个体来看,每个人的疾病都有偶然性和必然性,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所以我们今天对待生命、健康和疾病,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选择。小到感冒,有个人一个礼拜就好了,有的人却会迁延到一两个月,所以现在的医学追求精准治疗,也就是建立在更高层面上的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分析。现代的健康愿景追求全民、全要素,全流程,全方位的健康,有点像今天的奥林匹克运动要更高更快更强更健康。对于这种现象,传统的中医有一种反思,八卦里面有一卦叫飞龙在天,有一卦叫亢龙有悔,事实上人的身体在40岁达到峰值之后,慢慢就会往下走,所以这个时候不要求每个指标都处在最佳状态,平平常常就行了,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崇尚平人。
疾病与疾苦也不一样。疾病(Disease)是依据具体病因、特别的症状,实验室及各种现代医疗仪器探测出来的阳性指征所做出的偏离正常(健康)态的临床判定。疾苦(Suffering)则是疾病个体诉说的痛苦经历和身心体验,包含着社会文化投射。“一千个患者就有一千个胃病,一千个头痛……”、“一千个医生,就有一千个妙手回春”。生命也是有序和无常的共存,人生常态是生、老、病、死,也有没有病只有生、老、死的寿终正寝,或是只有生、病、死的未老先逝。同样的,死亡也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有无疾而终,有死于衰老,有不可预期的死亡,比如心脏猝死,也有可预期的缓慢的死亡,比如阿兹海默病……
学医的动机也存在个体和公共的差异,是否学医则是个性化的选择。报考医学专业的一般考量是就业机会、社会地位、职业收入等等,但个体的动机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协和医院妇产科的老主任林巧稚,她因为在考场上救人未能完成答卷,却被协和破格录取。著名的妇产科专家谭先杰,他学医的动机是因为他11岁时母亲离世,死于卵巢癌,他因此发愿要成为一流的妇科肿瘤专家,去拯救更多像母亲那样的女性患者。
前面讲到,医学有着多元的诉求,一方面要追求医学的真相,发现生命的真理,创造疗效,同时还要还原神圣,洞察真谛,创造更高的价值。所以每一个投身医学或者说献身医学的人,心中都要有两个词,一个是崇高,一个是神圣,否则的话很难往前走。因为成为一个好医生,不仅需要很高的学历,还需要跟人打交道的阅历,跟病人打交道的情感和情商,关怀病人的气质和气场,需要长期坚持的情怀和定力。医学是一个职业群,今天协和医院有将近90个亚专科。本科阶段学的是基础医学,硕士博士阶段才会进入二级分科。医学的成才周期是比较长的,按照吴英凯院士的说法,需要十五年才能达到一个高级专科医生的水平。
医学的最大问题来自职业社会属性带来的巨大的责任和压力,医生是社会精英,也是道德承重墙。医生的神圣光环,医疗技术的突飞猛进,带来社会的过度期许,尤其是过分道德化的期许。医生与患者共情,给予患者关怀,自己也需要他人的共情与关怀。渴望更多的理解与支撑。职场是竞技场,白色巨塔之中,同行之间龙争虎斗,难免遭逢不公,产生职业受挫与职业迷茫。医生岗位不仅需要专业知识与技能,还需要丰富的阅历与强大的心理素质,譬如,如何保守分享到的他人隐私,接触异性身体私密部位的本能联想,直面残酷的身心苦难,生死转圜的心理刺激与自我平复。患者的遭遇常常会唤起自己的个人经历和感受……面对这些挑战需要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

《孩子,你如果要学医》书封
我推荐大家读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佩丽·克拉斯(Perri Klass)是一个儿科大夫,也是一名医生作家,毕业于哈佛医学院,现任纽约大学小儿科和新闻系双聘教授,曾出版过三部小说、两本短篇故事集和两本医学散文。她给她的儿子写了十封信,集结起来就成为了《孩子,你如果要学医》这本书。她在书里说,在公众眼里,医生的形象是高收入、拥有尊贵的社会地位,在关键时刻救人于危难之中,拥有起死回生的高超医术,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还要看到背后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医患关系恶化,包括医疗事故的多发(根据国际上的统计,误诊误治的比例高达30%,因为很多疾病早期无法识别,等到可以识别的时候已经错过了窗口),让立志从医的年轻人有了更多的思考和顾虑。克拉斯就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如果选择学医,要掂量一下自己身上有没有八大禀赋:1、乐于跟人打交道,而非只是生物科学与理化技术的纸上谈兵;2、临床体检(触摸身体)总是第一位的,而非五光十色的理化生物检验;3、临床择科永远是一个难题,每一个科室都有自己的酸甜苦涩;4、独特的临床经验与共识、指南的困惑、冲突难以排解;5、诊疗总是不完美,医者跟医疗差错总是狭路相逢,越忧心,越冒头;6、保护患者隐私的意识必须时刻警醒,不可轻慢;7、遭遇患者濒死的非常时刻,医者必须全力以赴,逝者为尊,逝者为先;8、工作奉献与生活闲暇,家庭照料难以两全,总是顾此失彼。
和消防员一样,医生也是逆行者。在价值多元的时代依然追求利他的职业价值,明白利他即利己,助人即助己的道理。在一个漠视生命信仰的时代依然保持坚定的职业信仰。在一个缺少普爱价值的时代依然在诊疗中保持职业关爱的温暖,并不懈地传递着人间大爱。在一个诚信、规范稀少的时代依然保持质朴、纯粹的医患信任。在一个崇尚任性的时代依然保持敬畏悲悯之心……
另外,现代医学中有一个新词,叫做职业倦怠,或者共情耗竭。因为医学是高强度的,尤其是在住院医师阶段,时间压力巨大,需要在短期内接诊超量的患者。诊断治疗中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疗效常常不可重复。由于误诊、误治的普遍性,医护害怕发生医疗差错/事故,因而谨小慎微。频繁的疾苦叙事刺激,带来医护共情麻木,关怀迟钝。当遭逢不治之症(死亡降临)时,职业锐气受挫,感到无力与无奈。患者对于现代新技术寄予太高调期待,医护难以满足(做得越多,抱怨越多)。职业奉献得不到回报,医学人文的无功利性,导致利他情怀受挫。大众传播语境下医学知识普及化,带来患者对于医护权威性的怀疑。
今年3月,韩国因医学院扩招激起医生罢工辞职潮,引发社会大震荡。这个事件也必然会辐射到中国的医学教育领域。在中国,当下医学生淘汰率问题十分突出。在2024年中国医学发展大会上,王辰院士指出,当下医学生的淘汰率问题十分突出。2020年-2023年国家执业医师与助理医师考试通过率不到60%,2019年-2021年临床医学本科毕业生有30%根本不当医生。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也表示,目前我国医学教育总体招生规模较大,但整体层次偏低。过去20年(2002-2021),普通高等学校医学专业招生人数从23万增至125万,医学专业研究生招生数也从1.7万猛增至14万。由于培养模式多元和招生规模过大等原因,各校医学生培养质量良莠不齐。对此,王辰提出“医学专业招生要适量、限量、减量。”医学教育是精英教育,强调这一点并非是医学界自视甚高,而是因为医学关乎人类生命和健康这样的终极利益,只有高素质的人从医,才能保障生命的圆满。教育部网站发布的“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8780号建议的答复”中称,“医学教育的本质是精英教育。”
在美国,医学教育一直是精英教育,只在研究生阶段开设,不在本科阶段开设;精英教育的理念是要保持一定的淘汰率。尽管医学院的学生都是成绩优秀的,但整个医学教育体系还一直保持淘汰机制,确保留下来的都是最适合的。美国医学教育制度中,要想做临床医生,必须先有MD(Doctor of Medicine),但要想做学术型的医生,还要在MD的基础上读 PhD(Doctor of Philosophy)。多数情况下是以4+4的8年MD为主:4年的本科学习,毕业后进入医学院进行4年学习。如果是MD+PhD的话,需要在4年MD的基础上增加4-5年。美国波士顿凌晨发车的公交车里乘客不多,但大多数是哈佛医学院的实习医生/住院医生。他们必须在早7点前赶到医院,温习病历,准备查房与手术。协和沿袭百年的住院医师制度源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要求住院医生24小时值班。在杜克大学,无论你的本科成绩多优秀,如果要申请进入医学院学习,必须先完成约500个小时的义工服务,以证明你有照护他者、弱者的意愿与能力。如果没有义工服务经历,申请可能会被拒绝。
医疗服务中有一个3C/2H原理:Cure,治疗,由医生主导,护士配合;Care,照顾,由护士主导,医生协同;Call,回应诉求,由医护共同承担,甚至辐射逝后环节。医学要给人希望(Hope),其次才是疗愈(Healing)。医学比其他自然科学都要更复杂,这是由四个百年未变的特征决定的,即永恒的不确定性、生命的多样性、疾病转归的复杂性以及医患的主-客间性。威廉·奥斯勒医生曾经说过,医学是崇高的使命,而非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医学是一门不确定性的科学和可能性的艺术。医学是一辈子在学习,一辈子在付出,一辈子在收获,一辈子在反思,这是奥斯勒给年轻医生的忠告。生命/健康无常,它是一个谜局,一个灰箱,真相无法大白。人类不可能全知、全能、全善,人生路迢迢,也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不等式与万花筒。
(本文整理自北大博雅讲坛第600期,经王一方教授审定后刊发)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