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政变后,出于政治立场和施政理念的不同,清初以降隐而不现的南士和北士间的裂隙逐渐加深,因地域而形成的南北派系浮现。同治四年、六年,内阁学士李鸿藻、礼部右侍郎沈桂芬先后进入军机处学习行走。李鸿藻,字兰荪,号石孙、砚斋,直隶高阳人,同治帝师傅。沈桂芬,字经笙,本籍江苏吴江。二人的相继入值开启了所谓的“南北政争”。
李鸿藻与张之洞的堂兄张之万有旧交,因地域和旧交的关系,张之洞自然在南北政争中有所倾向。此外,李鸿藻、沈桂芬二人处理“洋务”观念的差异,亦是张之洞等人对南、北派系离趋的重要因素。有谓“北士以儒学正宗自视,标榜气节,南士重经世致用,强调务实,此右李、沈二人表现于参政风格上,差异殊显”。虽不免笼统其事,但在处理天津教案上,显见二人的区别。同治九年五月,因其时天津屡有人口失踪案,天津百姓怀疑法国育婴堂以幼童炼药,遂聚集于法国天主教堂前抗议。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Henri Victor Fontanie)持枪打伤到场的天津知府刘杰随员,引发群众愤慨。天津百姓砸毁育婴堂,焚毁海望楼教堂,并劫掠法国领事馆,殴毙包括丰大业在内的数十名洋人和中国教士。教案发生后,李鸿藻主强硬,沈桂芬等人则主转圜。翁同龢在日记中言:“兰孙以津事与宝(鋆)、沈(桂芬)两公争于上前,兰孙谓贾瑚言是,宜有明诏督责;宝、沈皆不以为然。上是李某言,故仍有明发。宝又云津民无端杀法国人,直是借端抢掠。李又力争。”在日后的中俄伊犁交涉中,张之洞表达了对沈桂芬等南士对外软弱的不满,谓:
总之,吴江(按:沈桂芬)昏谬私曲,既无公事之法,又不实修战备、调将帅,筹备将帅军火、筹借饷,百方阻止,惟其心必欲使大局败坏而后已,辅之以嘉定、常熟,祸不可言,事不可为矣。
张之洞与李鸿藻具体相交于何时不能确定,但可以确定同治初年二人已有交往。张之洞在同治元年(1862)、二年皆进京参加会试,也许曾拜见李鸿藻,但目前所见张之洞与李鸿藻的最早直接私下交往在同治三年七月初五日,《李鸿藻年谱》言其是日“寅刻入直,工课顺适。午后回寓少睡。张香涛来,党吉新后至”。此后在《李鸿藻年谱》中时常有张之洞前来拜望的记载。因交结李鸿藻,张之洞频放考差、学差。同治六年四月,张之洞充保和殿考差;六月奉旨充浙江乡试副考官;八月初一日,奉旨简放湖北学政;同治十二年,张之洞奉旨充四川乡试副考官,旋放四川学政。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十二日,《李鸿藻年谱》中记载:
张之洞函公云:“新诗四首,正得读否?上课诗卷,想无暇批阅矣!闷闷。前闻玉趾东游,由于后生撼树,外省传播,定当不虚。可否赐示崖略,至幸。敬上,名心叩。即丙。切。”
书信中如所谈之事不愿被他人知道,或有其他缘故,写信人往往不落款,而写作“名心”,意为收信人能知其为谁,心照不宣;“即丙”意为阅后即焚。信件所言之事暂不知为何,但从“名心”“丙”的字眼,可以看出应是私密之事。由此可见,最晚到光绪元年,张之洞与李鸿藻已有密商之事。光绪六年,李鸿藻倡建畿辅先哲祠,所祭祀者多为直隶先哲,“其一切归画,则公(按:张之洞)主之”。兴修畿辅先哲祠,不仅加强了北士的联络和地域认同,而且在筹建先哲祠的过程中,张之洞先后写了至少17封信给李鸿藻,讨论相关事宜,进一步拉近了二人的关系。

张之洞
尽管张之洞对南、北有所倾向,但并不意味着南士和北士间截然对立分离。经历咸丰动乱,同光之际京城文人交游诗酬、金石考订之风流行。同治九年十月,张之洞湖北学政任满,入都复命,居于南横街,与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陈宝琛诸人开始订交。其中江浙士人领袖潘祖荫与张之洞所居密迩,故常与张之洞通信论金石。通过这层关系,张之洞参与以潘祖荫为首的龙树寺雅集,并于同治十年共同宴请湖南名儒王闿运。
然而,出生、成长于边鄙之地贵州的张之洞,对金石、风雅之事并不如江浙南士擅长。《凌霄一士随笔》引鄂人卓从乾《杏轩偶录》所记张之洞嗜古器物而购买赝瓮受骗事,言“此或事属有因,不尽虚诬耶”。由此可侧面证明张之洞的金石功底。或因如此,张之洞其后逐渐关注时务。光绪三年(1877),张之洞四川学政期满回京。时惠陵竣工,照礼制穆宗(同治)帝、后神主应升祔太庙,然而此时太庙中殿九室已满,穆宗帝、后神主无处安放,惇亲王奕誴奏请饬廷臣会议。三月十四日,两宫颁布懿旨,命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同奕誴妥议具奏,引起王公、宗室、廷臣的激烈争论。在穆宗升祔的讨论中,张之洞虽无上奏的权力,却颇为留心,不仅与潘祖荫书信往返讨论,而且为潘祖荫代拟奏疏。张之洞所拟奏疏主张增建别殿以放神主,和其与潘祖荫书信中所表达的意见一致。陈宝琛云张之洞“自是究心时政,不复措意于考订之学”。张之洞的弟子樊增祥亦有同感,其致信谭献亦谈及张之洞“近(按:光绪四年)颇讲理学,学术又一变”。更重要的是,张之洞此时与张佩纶相知相交。张佩纶,字幼樵,一字绳庵,号篑斋。直隶丰润人,同治十年(1871)进士,父辈与李鸿章有故交情谊。据云张之洞阅张佩纶关于穆宗升祔的奏疏后赞叹不已,遂与张佩纶订交。张之洞、张佩纶二人不仅为直隶同乡,且都颇着意于时务,在二人的往来通信中,除了谈论聚会外,谈论政事者颇多。
同光之际,清廷屡次下诏广开言路,清议颇张。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光绪帝御极,诏曰:“朕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古来郅治之隆,胥由询事考言,嘉乃丕绩。我朝列圣御宇以来,俱颁诏旨,褒答直臣,广开言路,谏议时闻,寰宇欣欣向治。方今皇帝绍承大统,尚在冲龄,时事艰难,不得已而有垂帘之举。万机总理,宵旰不遑。因思人之聪明智虑,有所未周,必兼听并观,以通上下之情,措施方期悉当。矧当生民多蹙,各省水旱频仍,允宜博采谠言,用资治理。尔内外大小臣工,均当竭诚抒悃,共济时艰。用特谕知中外臣工、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当据实直陈。务期各抒所见,于时事有裨,而又实能见诸施行者,详细敷陈,不得徒托空言。”光绪三年(1877),因丁戊奇荒,张佩纶奏请广开言路,以拯时艰,上谕曰:“本年灾沴叠见,水旱蝗蝻之灾遍于数省,业经截漕发帑,蠲赈兼施。惟念吏治有无因循、民生有无怨恫、用人行政有无阙失,允宜上下交修,以图至计。尔大小臣工,务当各摅己见,切实指陈,总期广献谟谋,力祛积习,用副朝廷遇灾修省、从谏弗咈至意。”广开言路本是清代新主登基及遇有灾变时的寻常之举,然此时李鸿藻领袖“清流”,开一时风气。光绪四年,张之洞为詹事府左庶子黄体芳拟具《灾深患迫宜筹拯民应天之方折》,胪陈三条建议,即救急之道、治本之道、预防之道。其中治本之道有“斥奸邪”一条,痛诋南派官员、时任户部尚书和总理衙门大臣的董恂:
今朝臣中之奸邪,如户部尚书董恂是已。去冬以来,中外条陈荒政者,务从驳斥,雍遏上恩,膜视民命,全不知国脉邦本在于养民……以彼职长户部,天下户口财税,是其专职,然灾荒如此,宵旰忧焦,该尚书不闻进一言、画一策,已无解于溺职之罪矣!况加之以贪鄙欺罔、有心病国乎!其在总理衙门,言语猥琐,举止卑谄,通国皆知,其他为众口诋訾之处,罄牍难书。
结合日后“清流”于光绪八年弹劾董恂等人的行为,可以看出同光之际李鸿藻、清议已在政事上有所结合。因此折为张之洞拟具,亦可窥见其在此时政治上的取向。
光绪五年(1879)二月,张之洞授国子监司业,获上奏的权力。时吴可读尸谏一事引发朝野震动。同治十三年(1874),同治帝病亡无子,两宫皇太后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为嗣皇帝入继大统,即为光绪帝。光绪帝过继给文宗(咸丰帝)为嗣,而非为穆宗之嗣,如此两宫仍为皇太后,可继续垂帘听政。同时两宫颁布懿旨曰待光绪帝生有子嗣,即为穆宗之嗣。然而这使同治帝、光绪帝、光绪帝子嗣在帝统继承上出现紊乱,且颁立光绪帝子嗣为穆宗之嗣,有违清代秘密建储制度。光绪五年,同治帝归葬惠陵,闰三月初五日,随行之吏部主事吴可读服毒自杀,以尸谏的方式抗议两宫皇太后不为同治帝立嗣,其遗折痛陈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请两宫皇太后明白降下谕旨,将来大统仍归于光绪帝所生、过继给同治帝为嗣的皇子,以正名分而预绝纷纭。十七日,两宫发布懿旨,命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在宗室的缄默和纷纭的朝议中,张之洞之奏疏尤为巧妙,不仅将继统和继嗣合并,即请日后先挑选同治帝嗣子,再确定其为大统所归,而且明白将范围限定于仅讨论继嗣、继统并行不悖的方法,所谓:
臣恭绎懿旨中即是此意,妥议具奏二语文义。是者,是其将来大统宜归嗣子之意。议者,议夫继嗣、继统并行不悖之方。臣工应命陈言,岂敢以依违两可之游词,贻庙堂他日之筹虑。
张之洞之折维护了两宫皇太后的权力合法性,受到慈禧的青睐。光绪五年五月,前因四川东乡县知县孙定扬违规苛敛,激起民愤,后又请剿滥杀,张之洞据任四川学政时候之所闻,上奏请求再次复审东乡案,并奏参前护理四川总督文格。经刑部议奏,东乡案得以平反,朝廷将孙定扬等治罪,并命文格来京听候部议。平反东乡血案一事为张之洞博取了直声。其后,张之洞与张佩纶、陈宝琛、宝廷、黄体芳、邓承修等相互引援,隐奉军机大臣、北派领袖李鸿藻为首,以清议大张声势。时翰林院侍讲王先谦已觉言路渐渐彼此唱和,迹涉朋比,六月十七日,其上奏言路宜防流弊,请旨饬谕以肃政体。廷旨谕以言路不准同词附和,致滋流弊,但仍准言事诸臣于政事缺失、民生利弊各抒己见。
张之洞此时所经营的“南城士大夫”交游,逐渐形成其政治底色。通过这层交往,张之洞与洋务领袖李鸿章也有了间接联系,为他日后的“洋务鸣世”奠定了基础。目前所见,张之洞与李鸿章最早的直接交往在同治八年。其时李鸿章因镇压太平军、捻军有功,授湖广总督,于同治八年正月抵湖广总督任,十二月督师赴黔,随后湖广总督由其兄李瀚章署理。张之洞则于同治六年奉旨放湖北学政,直到同治九年任满回京,其间与李鸿章同城为官接近一年。这一年,张、李二人虽在创设经心书院上合作,但张之洞显然不快。如对家人言有掣肘之感,称:“至此官与人相处动须迁就,绝不能一意孤行,崭然自立,面目殊令人不快耳。”李鸿章曾就郧阳发生的胡树棻学案致函张之洞结案,并为草率处理此案的郧阳府知府求情宽免。显然,张之洞对于督抚、州县官插手学政事务颇为不满。同治九年八月,李鸿章因处理天津教案,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随后兼任北洋大臣。同光之际,清议兴起,但李鸿章对李鸿藻和清流物议颇不以为然。在处理滇案的过程中,他曾写信给其兄李瀚章,表达对当轴和清议的不满。除了办理洋务意见不同,李鸿章对所谓“南城士大夫”肆意弹劾亦不谓然,对张之洞入奏的东乡案及郑溥元弹劾山东巡抚文格一事评价道:“星轺四处,大非佳事,都人亦有私议,盖上意事从严,当轴间有迎合。今日封疆真不易为,难保终必无查办之举,可惧也。”
然而,李鸿章曾有意拉拢提携张佩纶、吴大澂等人,通过这层“南城士大夫”的交游关系,张之洞与李鸿章有间接的联系。光绪四年(1878),因河间府灾情严重,李鸿章奏派吴大澂、盛宣怀、李金镛筹集赈款。在吴大澂的倡议下,籍贯直隶南皮的张之洞公捐之余,另筹集白银1560两,事后李鸿章为诸人请奖。五年,李鸿章母亲八十大寿,在此之前,张佩纶、张之洞等人就谋划以文字向李太夫人祝寿。据《张佩纶日记》记载,光绪四年十一月初九日,张佩纶邀约陈宝琛,请其修改寿文序言;张之洞则作《合肥李相太夫人八十寿诗》祝贺。但由于观念和交游圈子的不同,张之洞、李鸿章二人在光绪六年以前,除了在湖北,并无太多直接的交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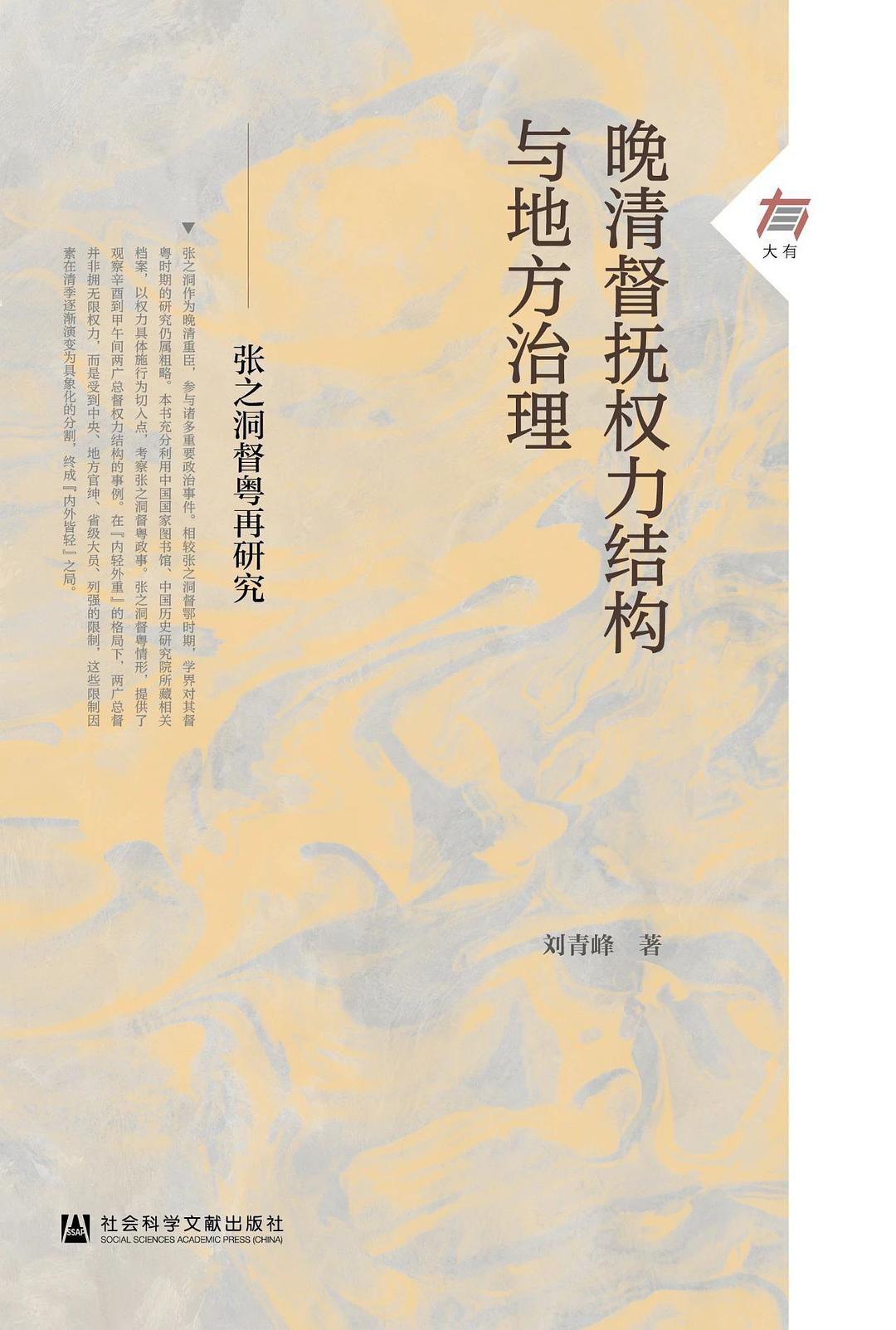
(本文摘自刘青峰著《晚清督抚权力结构与地方治理:张之洞督粤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5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