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南希·阿姆斯特朗(Nancy Armstrong,1938—),美国杜克大学英语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18—20世纪英美小说、文学批评理论,论著广泛涉及文学与资本主义、个体化、性别、图像文化等领域的关系。作为其代表作,《欲望与家庭小说》一书聚焦看似与政治无关的家庭小说,这些小说隐含了现代个体的形成、中产阶级的兴起等重大历史进程的秘密。18世纪的家庭小说为英国中产阶级的兴起铺平了道路,家庭和女性成为冲击旧贵族的道德观念、经济模式等的突破口;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女性的欲望转而以“疯女人”的形象出现,被视为家庭混乱、社会动荡的根源;而到了20世纪,随着精神分析话语的兴起,女性主体又以另一种方式被书写。全书深入理查森、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伍尔夫等经典家庭小说作家的作品,揭示了女性主体的书写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摘自该书,澎湃新闻经上海人民出版社授权发布。
从《帕梅拉》到《爱玛》,我们从理查森在文化中开辟的广阔而杂乱的领域,转向奥斯丁简约主义艺术的简洁线条。尽管奥斯丁的虚构作品更接近于我们所认为的“小说的艺术”,但是,它们同样具有政治色彩,因为它达成了理查森作品所欠缺的自我封闭性(self-enclosure)。很明显,在奥斯丁的时代,女性主体可以作为知识的对象走上前台。理查森必须同时修改虚构作品和行为手册的语言,以此为家庭小说建立一个范畴;而不同于理查森,奥斯丁能够在家庭关系的一个稳定框架内发展微妙的差异。事实上,她的小说将淑女小说的传统推向高潮,这类小说聚焦于保障良好姻缘所必需的行为规范中的细枝末节,也就是受人尊敬之人的轻度不慎和良好举止,而不是聚焦于在迫近的强奸面前保护贞洁所需的意志和机巧。理查森用强奸来象征更早期的阶级性态。这被他囊括进了虚构作品,在其中强奸确认了一个不可侵犯的自我。通过这样做,他利用这个女人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抵抗形式。以这样一个独特的现代自我概念为前提的写作——帕梅拉对她的情感遭受攻击的记录——也阐明了理查森所面临的历史困境。他的写作需要得到读者的授权,才能声称是真实的。理查森让帕梅拉带着奇怪的习惯穿梭在她丈夫的高雅朋友圈中,扮演着家庭圣人的角色,就好像这种授权是将帕梅拉与贵族的婚姻神圣化的仪式之一。她带着那些讲述她在一个放荡的主人的统治下坚守阵地的故事的信件,以这样的形象寻求着公众认可。如果没有这种认可,结果将是,她的写作只不过是主观经验的一次记录,一个不加掩饰的愿望(事实上菲尔丁就是如此看待的),而不是一个人人应当用以协调现实的榜样。这个女人跟她的写作绑在了一起,形成一种互相授权的关系,在小说的结尾,这种关系笨拙地展示出自身循环论证的属性。
然而,令菲尔丁大为沮丧的是,理查森成功地将如下高度虚构的主张引入了虚构作品,即一个富有的男人最渴望的是一个体现着家庭美德的女人。而在奥斯丁的时代,这一主张已经获得了真理的地位。它已经取代了旧有的主要规则,亦即朱克斯太太在责备帕梅拉否认主人对女佣身体的自然支配时提出的那些规则。在此基础上,可以说,一部像《傲慢与偏见》这样的小说,从历史角度来讲,是在《帕梅拉》的结尾处开始的——前者以“一名富有的单身男子,一定想要一个妻子,这是公认的真理”作为开头。通过将“妻子”描绘成一个需要填补的范畴,而不是一个有待开启的欲望的范畴,虚构作品显然不再与真理对立,也不必进行精心的自我授权仪式。显然,奥斯丁的读者欣然接受虚构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真理形式的地位。这种权威的关键是自我封闭性。就像伯尼和其他女性小说家一样,奥斯丁似乎更愿意抛下世界的其他一切地方,只处理求爱和婚姻的问题。如果说理查森在小说中引入了行为手册的材料,作为一种转换策略,那么,世态小说(novels of manners)则确立了各种管束策略(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它们似乎并没有从家庭内部开始运作,以产生一种能够彻底改变其语境的文本。但是,通过将她文雅的英文与她从早期小说家那里继承来的语言材料区分开来,奥斯丁的小说甚至比理查森的小说更有效地实现了同样的政治目标。

1996年版《爱玛》电影剧照
她的小说描写一个封闭社区中的高雅乡村人士,他们往往是非富亦非贵的普通人。在这样的社区中,社会关系看起来几乎和家庭关系是一回事。因此,社区能够以家庭和家庭之间关系的话语来描绘,跟《熟能生巧的佣人》一书中对各种家庭生动描述的方式几乎是相同的(这是一本关于家庭经济的书,写作时间跟奥斯丁创作《爱玛》的时间差不多)。就像在行为手册中一样,奥斯丁描绘的世界里有待面对的问题都跟空闲时间的管理有关。奥斯丁解决这些问题一贯是靠让社区内的合适人选出嫁,也就是将其固定在诸多家庭中的一个家庭之内的一个角色,以此稳定该社区。此外,她是按照在心理学标准上严苛的规则来这么做的,其严苛程度不亚于在考虑实利的婚姻中起决定作用的嫁妆和家族关系等问题。她从文雅乡绅的言谈举止中为两性关系发展了一种复杂而精确的语言。而且,我们应该注意到,她这么做的时候,向城市的大迁移正在发生。因此,像她这样的语言,帮助创造了一种文雅英语的标准,并为新近兴起的阅读小说的群体所共享,这是文化史上的一个奇特转折。似乎只有这种专门的语言,才能把他们特定类型的文化教育与社会阶梯上处于他们上层和下层的文化教育区分开来,同时,把这一阶级的特定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区分开来。如果承认理查森的小说使文化教育在建构个人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新的角色,那么我们必须看到,奥斯丁的小说努力赋予一个新的阶级以权力——不是有权势的人,而是普通人——他们诠释人类行为的能力,使他们有资格去规范日常生活的行为,且在写作中并通过写作再生产他们的个体形式。
以一种理查森和18世纪晚期的淑女小说家特有的方式,奥斯丁用虚构作品创造了一个社区,这个社区没有任何地区、宗教、社会或政治派别的方言的痕迹(而其他类型的写作正是以此为特征的)。蒙德·威廉斯解释说,在18世纪初,男性教育机构非常混杂,也许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混杂。他说,在复辟后由不信奉国教者建立的高等中学或大学水平的学校,“课程开始呈现现代形态,加入了数学、地理、现代语言,最重要的是,还有自然科学”。他接着说,九所文法学校中,“有七所是寄宿学校”,都“主要保留了传统的古典课程,虽然它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排外,但总体上倾向于为全国的贵族和乡绅服务”。除了这些学校之外,上层阶级还遵守在家里进行家教的做法,与此相随的常常是到欧洲大陆的壮游(Grand Tour)。根据布莱恩·西蒙的说法,绅士的标志是“不获取任何专业知识;目的是通过学习古典著作来了解高雅文学”。接受资助的文法学校显然根据地区而有所不同,那些在城市地区的学校,在从事商业贸易之人的影响下,显示出课程会朝着实践学科有一些拓宽。威廉斯总结道:“在三种古老的职业中,神职人员依旧主要由大学培养,而法律和医药从业者则大多在大学之外培养。那些新兴职业,尤其是在科学、工程和艺术领域,大多数新从业者在大学之外接受培训,就像大多数商人和制造商一样。”尽管在教育的许多层面和不同区域,课程都日渐显示出实践的特征,但早期现代社会的中间阶层的教育看起来仍然构成了一种非常多样化的学习领域。然而,一种在我们现在看来十足杂乱的写作风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许会显得更有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各种专门化的语言被精确地划定了上下等级。
这些人既不同于受过高雅教育的人,也不同于文盲的大众。然而,与此同时,他们所学的东西会标示出他们之间的差异,而非创造一种一致的社会性格。如果像威廉斯所说的那样,教育机构的意义总是在于培养“一个群体中的成员,使之具有在群体中占主导地位的或者群体赖以为生的‘社会特征’或‘文化模式’”,那么只有贵族和乡绅才能被认为具有这样的特征。从18世纪一直到19世纪,特权群体之外的男性人口不仅因为他们的所学、所谈和所写而与前者区分开,他们彼此之间也相互区分开了。一个人使用的语言会立刻表明他的身份是一个英国国教成员还是不信奉国教者,是一名接受古典传统教育的学生还是一名实践课程的学生,是使用高雅英语的精英群体的成员还是使用不登大雅之堂的方言的精英群体的成员。
在话语模式和写作风格的这片混乱中,奥斯丁追随了由女性行为手册开辟的道路。与此同时,必须要说,奥斯丁将开创另一种高雅写作标准的事业往前推进了一步。如果说理查森是用帕梅拉的写作来改变她社区的话语模式,那么奥斯丁则是让写作根植于高雅的乡村人群的话语之中。她自己的表达方式替代了更能精确代表社会整体的混杂文风。因为她的社区是一个话语的社区,分享着恰当的名词,但奇怪的是,社区中的人看起来困惑于他们各自的价值,以及他们之间应当存在的关系。因此她创造出一种文风,能够在高雅的口头英语范围内,展示无数种不同个体类型。通过对话、流言蜚语和私人信件的方式,这样的写作将动机和感受赋予社会行为,并以这种方式为社会行为的意义创造心理基础。这种文风将话语社区的成员相互区分开来。与此同时,它从主体性特征的层面,将个体与个体联系起来——这些主体性特征能够被作为整体的社区所理解。如果这是要仅凭一种关于自我的共同语言就建立一个社区,那么,当奥斯丁用语言来指向个体内在的品质而非偶然的财富和出身时,语言本身就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稳定性。因此,奥斯丁的小说将理想社区的形成等同于一种新的高雅英语标准的形成。
虽然奥斯丁的虚构作品与早期的家庭小说一同参与了一个文化事业,但我们还是要将她的作品与早期虚构作品区分开来,因为她将其理想社区更深地根植于交流之中。奥斯丁的目标不是要反驳作为旧社会基础的等级原则,而是要重新定义财富和地位,因为大量的关于财富和地位的标志必须以语言这种更为根本的通货来进行阅读和评估:它们传达了多少信息,又有多准确?人们发现,她小说中的主要事件都是基于错误的交流:蒂尔尼上校将凯瑟琳·莫兰误解为一位继承者,而她将他误解为一位丈夫和父亲;达西写给伊丽莎白·班内特的前后两封信的对比;曼斯菲尔德庄园里戏剧化的娱乐;以及一系列这样的片段,让《爱玛》中行为举止的问题几乎完全成了阐释的问题。例如,可以想想爱玛对哈里特·史密斯的描绘,她对埃尔顿先生字谜的阐释,以及对小说中其他适婚年轻男子所写信件的阐释,面对奈特利对她错误阐释的批评所做出的辩护,还有她意识到自己对他真实的感受。阅读和写作的步骤从纸页延伸到了舞池和客厅。它们暗示两性关系首先是一种语言契约。并且,由于小说将它的演出场景局限于一个社会关系由两性关系决定的框架之内,语言契约就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契约。
奥斯丁的小说演绎了理查森式的主题,女性话语为了赢得代表个体身份的权力而与男性话语相抗争。女主角又一次假定了一种建立在性别差异而非政治差异之上的性别观念。男人遵循政治差异,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他们的权威。但是一些改变已经在《帕梅拉》的发表和《爱玛》的写作之间悄然发生。主仆之间的距离已经显著缩小为一个精英群体,其中的个体既非贵族也非劳动者,甚至不是商业或产业阶级。与此同时,由精确的差异构成的一整个谱系已经在这个与政治的关联受到限制的领域里打开。这些差异包括:表明一个人收入来源的传统政治标志,一个庄园和家族的名字中带有的声望,以及一个有资源的人恰好能展示的外在标识:文雅和教育。这些社会标识使人想起18世纪晚期的乡村绅士阶层,在前一个世纪的经济波动中,乡村绅士阶层已成为一个极其多样化的群体。在这样的一个群体中,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无疑是很难辨认的。但在奥斯丁的作品中,这种情况更加复杂;当地的交流系统,即流言蜚语,将传统的地位标志与它们在经济依赖链中的所指分离——流言蜚语系统自动地将这些信息转化为主观经验。例如,奈特利先生可以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说:“埃尔顿是个很好的人,也是海布里一个很受人尊敬的牧师,但他在婚事上绝对不会轻率。他和任何人一样知道一份好的收入的价值。埃尔顿说起话来也许感性,但做起事来会是理性的。”爱玛却不以为然:“她非常肯定,埃尔顿先生所具有的,无外乎是合理而适度的谨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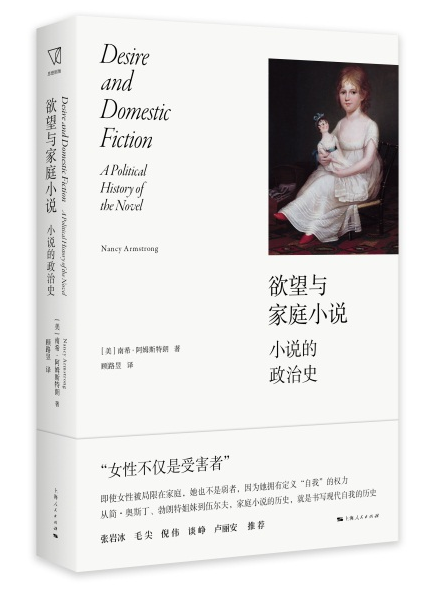
《欲望与家庭小说》,[美]南希·阿姆斯特朗著,顾路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8月。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