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著名美籍华裔作家、翻译家聂华苓在美国爱荷华家中去世,享年99岁。她的女儿王晓蓝发布消息,称母亲“走得很安详,没有太多痛苦。”
这阵子,王晓蓝恰好来北京。10月14日离开爱荷华之前,她上楼坐在妈妈床边,对她说:“妈妈,你一定要等我回来。”聂华苓说:“我当然会等你。”王晓蓝又亲了妈妈的脸,说“我爱你”,然后聂华苓说:“我也爱你。”
“有人说她选择我不在的时候离去,因为她怕我伤心。”妈妈离开后,王晓蓝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聂华苓与丈夫保罗·安格尔
一生,一棵大树
对于自己的一生,聂华苓曾形容:“我是一棵大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
聂华苓1925年生于武汉,1948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外文系,同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49年与家人到台湾,1964年旅居美国,任教于爱荷华大学,代表作有小说《桑青与桃红》、回忆录《三生三世》《三生影像》《三辈子》等。
1967年,聂华苓与其先生、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在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的基础上创办了“国际写作计划”,每年在世界范围内邀请作家前往。至今,“国家写作计划”已邀请来自100多个国家的上千名作家前往爱荷华进行创作与交流。世界各地作家齐聚一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尔罕·帕慕克、切斯瓦夫·米沃什、谢默斯·希尼、托妮·莫里森都曾参加过这一计划。聂华苓也因此被誉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
青年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李浴洋详细梳理过“国际写作计划”的发展历程:1967年创办后,不同国家、种族与文化立场的作家在这里相聚,借用聂华苓的话说,他们“交流”而非“交锋”。在20世纪后半叶充满对峙与斗争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国际写作计划”发挥的作用尤为引人关注。

聂华苓
1978年,聂华苓访问中国大陆。次年,她与安格尔在“国家写作计划”中发起了“中国周末”活动,邀请中国大陆作家陆续赴美。
通过“国际写作计划”,萧乾、艾青、王蒙、丁玲、茹志鹃、王安忆、谌容、徐迟、冯骥才、张贤亮、阿城、古华、汪曾祺、北岛、残雪、苏童、西川、李锐、蒋韵、余华、唐颖、陈丹燕、莫言、刘恒、迟子建、毕飞宇、胡续冬、格非、韩博、徐则臣、金仁顺、阿来、王家新、张悦然、周嘉宁、笛安、石一枫、索耳、王占黑等几代中国大陆作家都来过爱荷华。
她是快乐的源泉
在许多作家的印象里,聂老师特别爱笑,经常大笑。日渐衰老的躯体,并不能关住一颗一直生动的心灵。

“她的家在山坡上,太多作家去过她家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肤色,不同的信仰。”毕飞宇于2006年参加“国际写作计划”,他记得那一年一共有26个作家,来自24个国家。大家每天都在一起,吵吵闹闹的,“那三个月无限珍贵。”
毕飞宇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聂华苓是一个拥有无限能量的人,热情,特别热心于助人。当然,她也有脾气,几乎不掩藏。“我和聂老师之间有过许多美好的时光,我时常回忆起我们在一起的时刻。”
在爱荷华,毕飞宇记得聂华苓一直在请吃饭。“她对所有去爱荷华的中国作家都这样,不停地请大家吃饭。她家里有一张椭圆形的餐桌,像一个微型的足球场。这个家的主人显然知道家里会来许多客人,餐桌就比一般的餐桌大一些。所有的客人来了之后,都会在这张桌子的周边,海阔天空。”
“她是快乐的源泉,大嗓门,同时对快乐的反应也格外敏捷。她永远是第一个大笑的人。听她的笑声,你以为她是一个大块头,实际上聂老师身量很小,但她能量充沛。”

苏童、聂华苓、迟子建、毕飞宇
毕飞宇说,聂华苓八十多岁的时候还在开车,就开着车带他到处逛。等到2017年——“国际写作计划”50周年,他第二次来到爱荷华,聂华苓已经年过90岁。“她失去了心爱的驾照,很失落,不止一次对我说,没有了车,就失去了自由。”
“我最后一次见到聂老师就是2017年,分别时痖弦也在,还有他的两个宝贝女儿。我们就围坐在那张桌边,足足有两天的时光。除了睡觉,我们都在一起。我猜,聂老师和痖弦都知道,那是他俩最后一次见面了。现如今,他们都走了,我格外怀念那个小小的足球场。”
无畏、透明和光华
作家迟子建一直记得初见聂华苓时的场景。那是2005年,她和刘恒受“国际写作计划”之邀去美国展开为期三个月的交流和访问。抵达爱荷华时已是深夜十一时许,八十岁的聂华苓一直在家等着,一见面就热情地拥抱迟子建和刘恒,叫着:“你们能平安到,太好了!”
在《一个人和三个时代》一文里,迟子建回忆了当时的许多细节:“一上楼,我就闻到了浓浓的香味,她说煲了鸡汤,要为我们下接风面。她在厨房忙碌的时候,我站在对面看着,她忽然抬起头来,望了我一眼,笑着说:‘你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我笑了。其实,她跟我想象的也一模一样!有一种丽人,在经过岁月的沧桑洗礼和美好爱情的滋润后,会呈现出一种从容淡定而又熠熠生辉的气质,她正是啊。”
那年在“国际写作计划”的最后一夜也给迟子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天渐渐黑了,大家生起火,围炉喝酒谈天。谈着谈着,聂华苓忽然放下酒杯,引大家来到卧室,拉开衣橱,取出一套做工考究的中式缎子衣服,斜襟,带扣襻的,银粉色,质地极佳。聂华苓举着披挂在衣架上的那身衣服,笑吟吟地说:“我已经嘱咐两个女儿了,我走的那天,就穿这套衣服!怎么样?”那套衣服出水芙蓉般的鲜润明媚,迟子建说:“穿上后像个新娘!”
“她大笑着,我也笑着,但我的眼睛湿了。没有哪个女人,会像她一样,活得这么无畏、透明和光华!”
石一枫第一次见到聂华苓是在去年中秋,他和索耳、王占黑一起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因为疫情,这一场见面迟到了三年。
“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吃面条,晓蓝老师做的牛肉面。那会聂老师记忆力已经不太好了,她就问我来这之前,见过哪些来过爱荷华的中国作家,我说见过毕飞宇老师,迟子建老师,他们都向你问好,然后没吃几口,她又开始问我见过哪些作家,反反复复的。但其实我很感动,一个老人,记忆力已经不好了,但还是那么记挂中国的作家朋友们。”
石一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那时聂华苓已经年近百岁,身体没有太多力量,但他依然能感受到她的坦荡与热情。“她很爱笑,特慈祥,一直都是笑呵呵的。”聂华苓还和石一枫说起他一本书的题目,说会起这么个题目,可见是会写东西的一个人。
“那天我们离开聂老师家里的时候,正好红房子上是一轮圆月,聂老师就在门口和我们告别。现在想想那个景象,挺美的,也挺有感触的。”石一枫说。

《三生影像》
她不仅是“伯乐”,自己也是一匹“千里马”
在石一枫看来,在“国际写作计划”,有两点弥足珍贵,一是开阔了视野,二是能真正去了解世界各地的作家们都在关心什么。
得知聂华苓去世的消息,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主任Chris Merrill给王晓蓝发去这样一段话:“对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作家来说,这是多么悲伤的一天。能认识她,爱她,对我来说是多么大的幸运。她会永远留在文学史上。我们会尽我们所能,维护她的愿景。”
李浴洋注意到,作为国际性的作家交流平台,“国际写作计划”虽然也邀请功成名就的作家参加,但他们所占的比重其实很低,大部分名额留给了尚在成长中的年轻作家。而几乎所有中国当代的重要作家,在其崭露头角时,便都会进入聂华苓与安格尔的视野并得到她的帮助。因此,聂华苓与安格尔受到了国际文坛的高度评价与普遍尊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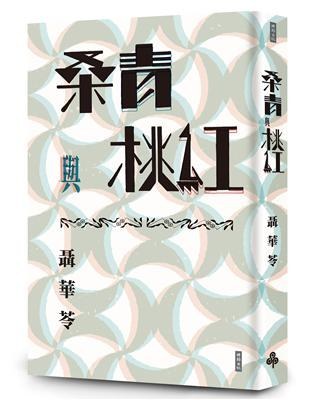
《桑青与桃红》
但在李浴洋看来,阅读聂华苓,不应忽略在她外在的活动与内在的人生的接榫之处,除却一桩桩文学因缘,还有她一部部文学创作。早在1959年还在《自由中国》杂志社担任编辑时,聂华苓就已经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翡翠猫》。次年,她又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此后的《桑青与桃红》更是奠定了她作为华语文学经典作家的地位。继而,她又有多部短篇小说集与长篇小说问世。
“她是创作、翻译、评论与研究的多面手,其中尤以小说创作与翻译见长。换言之,她不仅是‘伯乐’,自己也是一匹‘千里马’。只不过日后作为‘伯乐’声名日隆,以至掩过了她的作家本色。”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