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3日至9月25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办,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协办的第十九届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顺利举行。今年研讨班的主题是“旅行史:全球化的网络与形式”。来自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法国社会高等研究院、法国第三大学、格勒诺布尔大学等机构的七位专家学者进行授课,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温州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科技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等国内高校与科研院所的50多名教师与硕博士研究生参与了研修。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朱明教授为开幕式致辞,他指出,今年的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迎来了20周年纪念,从旅行史的角度看世界史,可以补充以时间为主线的历史叙述,商品、人、思想的流动构成了旅行史的内容,研究者需串联过去与当下,比较世界不同区域,从而通过书写旅行史来更好地认识世界,理解当下。二十年来华东师大历史学系的中法合作,延续了法国的优良史学传统,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拓展,有所创新。中国法国史研究会荣誉会长端木美研究员以热烈的致辞表达了对本次研讨班中外交流的殷切希望,并对所有参会的师生学者表示热烈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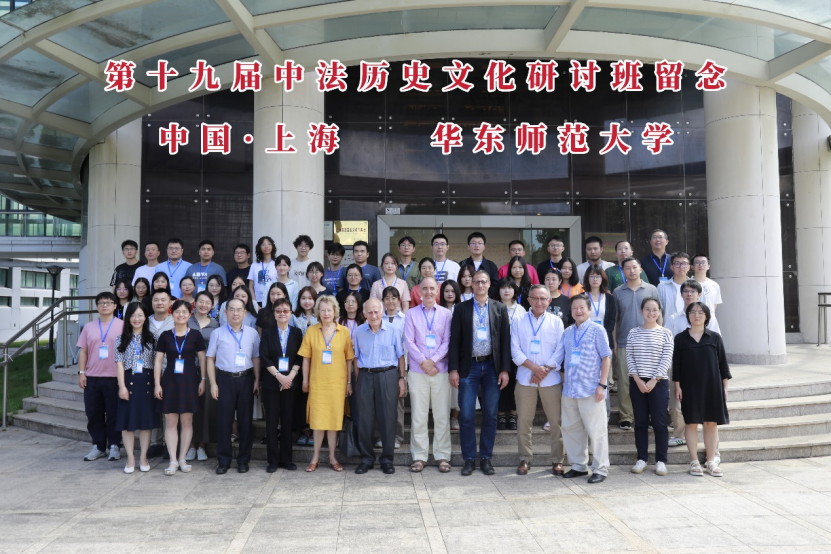
与会者合影
与会学者为研讨班全体师生学员带来了六场体现了最新学术前沿的报告。
9月23日上午,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的莫里斯·埃马尔(Maurice Aymard)教授做了“植物的旅行:甘蔗与蔗糖征服全球的历程”的报告。在全球史当中,以一种经济作物为主题的研究并不少见,埃马尔教授在本次讲座中除了以甘蔗、甜菜这两类经济作物为主题以外,还通过人类对甜味的需求串联了这两种作物在全球范围的旅行,并以长时段视角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通过他的讲座,我们对如何结合旅行史与全球史的研究得以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他开篇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强调一种作物的历史?教授认为这是一种沉默的历史,因为蔗糖流动的主要参与者往往留下的记录不多。围绕这个问题,埃马尔教授首先介绍了蔗糖流动的大背景——植物在不同地域的分布受到人类的影响,而哥伦布为亚洲作物从阿拉伯世界进入美洲奠定了基础。蔗糖起初并不是一种必需品,南亚地区的人们对它的利用方式还处于一个原始阶段。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首次将甘蔗从印度带回,但并没有大规模种植。相较于蜂蜜以及含有果糖的水果,甘蔗作为甜味剂的地位并不重要,就像当时人们对蔗糖的描述:“一种没有蜜蜂劳动的甜味”。中世纪威尼斯与热那亚的商人从阿拉伯人那里进口,再转卖到欧洲;同时在气候温暖的西班牙南部开始种植甘蔗,并请阿拉伯的制糖工来帮助加工蔗糖。他还提到,在甘蔗传入后,美洲迅速将耕地甚至是开荒的林地提供给甘蔗种植,解决了欧洲土地肥力不足、面积不足的问题。由于甘蔗种植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与甘蔗种植面积扩张同时发生的还有奴隶贸易。直至19世纪初拿破仑推行大陆封锁令之时,为打破封锁遂从安的列斯群岛和巴西地区运来甘蔗制糖,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的的大规模制糖才出现。教授强调,蔗糖其实是人类“创造的食物”。同时,原来作为蔬菜的甜菜也被利用为制糖原料,来弥补蔗糖产量的不足。庞大的市场需求促使糖在生产中不断改进工艺、质量,蔗糖的全球化流动是工业化的结果。与工业化制糖相对的,城市化也改变了人们对糖的需求。工业化以前,糖的消费主要作为一种甜味剂。三角贸易从美洲归程欧洲,除了携带金银之外,糖类也是重要货物之一,在欧洲精加工后供给贵族。工业化时期,人们尤其是城市劳动人口对能量的需求增加,糖的主要消费目的变成了供给能量。埃马尔教授还补充了一些关于糖的需求是否由人为因素促进的看法。制糖业发展的高峰期在最近六七十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配给制,糖的消费受到限制;战后则是糖消费迅速发展的时期——糖的应用从医药、家用逐步扩展到烘焙和其他行业。接着埃马尔教授总结了甘蔗制糖在发展历程中大都是不连续的,全球性的制糖业直至晚近才发展出来;而甘蔗与甜菜的种植、制糖和推广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由亚洲传向欧洲、非洲并最后到达美洲的过程。埃马尔教授还提供了一些针对蔗糖起源、古代制糖业的研究,并探讨了启蒙时期大规模用糖引起启蒙思想家对奴隶制的批评这一问题。

23日下午,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米海伊·科尔比埃(Mireille Corbier)教授围绕“罗马帝国:在流动性与非流动性之间:个体与群体流动轨迹与文化遗存的分析”这一题目做了报告。科尔比埃教授不仅深入解析了罗马帝国各个阶层在地中海区域的旅行,同时还关注了在当时几乎平行存在的两大帝国——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在城市内部流动性方面的差异。这样的旅行史研究成果说明,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可以融入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双重视角、双重关怀,以此产出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成果。科尔比埃教授接着开始介绍罗马帝国中流动的三种形式。首先是使节的流动,它主要发生在地中海世界的中心——罗马城。共和国时期,各个城邦都有向罗马派驻使节或使团,以达到各种目的。她以希腊派往罗马的一个哲学家使团为例,他们不仅在元老院演讲,也在贵族家中或是广场上演说,最后达到了减少雅典城邦罚款的目的。帝国时期,使节的流动主要是为致敬皇帝的生日、婚礼等重大场合;到图拉真皇帝时,开始允许城邦以法令形式代替使团进行致敬。第二种流动是罗马皇帝的出巡,他们经常在帝国境内进行巡视。教授介绍了一本1951年由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写的《哈德良回忆录》(Les mémoires d’Hadrien),以书信体的方式介绍了哈德良的出巡;此外他建造的阿德里亚纳别墅,很多建筑的命名就来自他巡游时的经历。除了建筑,当时铸造的纪念意义的铜币也刻画了皇帝出巡各个阶段的景象:入城仪式、进入军营、拜谒神祇等等。这些铸币也是帝国内流动性在地方留下的痕迹。第三类流动则是特定人群的特殊活动,它们多是运动员、艺术家群体为了参与不同城邦举办的表演或竞赛产生的流动。科比埃尔教授指出,原来这些竞赛大多集中于东部地区,罗马皇帝则有意识地将其移植到西部、迦太基,以保障娱乐活动的供给,调动民众的热情,甚至为此推出过赛事年历。这些有组织的赛事安排就使得帝国境内的艺术家、运动员经常处于奔赴其他城邦的状态,自然就留下了很多记录。教授展示了一些“马赛克”艺术,它们多见于贵族们的豪宅装饰。其中既有突尼斯的体育竞赛、西班牙的戏剧表演赛,也有意大利出土的船只运载非洲表演大象的画面。这些考古遗存能够为我们研究罗马帝国特定人群的流动提供帮助。最后,她总结了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城市的主要异同。两者都是通过征服奠定版图,疆域和人口数量相近;两者都有一定规模的城市,但人口以农耕人口为主,展现了其非流动性的一面。两个帝国的区别主要在于城市分布和国家治理方式上。罗马帝国的城邦中心实质上是一种公共空间,其中包含了政治活动、司法活动和经济活动。城邦之中的大型建筑大多是为公民提供娱乐活动的,这一点与汉帝国的城市有所不同。科比埃尔教授的两大帝国对比研究,为在场师生提供了研究方法层面的启发。

9月24日上午的第一场讲座的主讲人是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艾迪安·布尔东(Étienne Bourdon)教授,主题是“16世纪至1860年中欧之间物的旅行”。在旅行史的研究中,布尔东教授一向注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此次讲座中,他将旅行史研究与地理学、制图学、图像史等方面的成果结合起来,将这一时期物品的旅行作为折射研究社会、文化、消费等方面的窗口。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式生动地展示了旅行史作为历史学领域的新学科的前景与活力。接续上文,教授提出讲座的三部分内容:商品的旅行、知识对象的旅行以及旅行的物品背后的文化与地缘政治。第一部分商品的旅行,他主要介绍了这一时期中欧之间大宗商品的流动。最重要的当属贵金属自欧洲国家到中国、日本再流动到南美洲或欧洲这一线路,与之密不可分的是当时中国对贵金属的需求和地理大发现增加了南美运抵欧洲的银产量。此外,铜矿也是重要的商品之一。其次,自16世纪后,中国商品开始逐渐流行于法国精英阶层。教授举了两个例子——黎塞留遗产中的瓷器和马扎然拥有的大量的绢纱。同时从中国返回法国的商船数量也很大,例如第一艘直接远航中国的商船——安菲里特号。它将带回的货品进行拍卖后获利高达150%,可见远洋贸易对商人和王室都是暴利产业。不过教授也指出,安菲里特号来到广州后,水手就待在十三行地区,贸易也通过十三行的商人,接触到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其实是有限的。他还以船公司的拍卖广告和茶叶、瓷器的进口统计表展现了中国商品进口量的迅速增长。风靡一时的中国商品也为法国的中国风格画派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进入第二部分,布尔东教授展示了书籍文本、书信的流动。中欧之间的文本交流往往不是直接的,而是要经过波斯湾等中继。耶稣会士来华带来了地图的绘制,不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同时欧洲的托勒密绘图传统也与中国传统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绘图技法。另一方面,随着传教士而来的地图测绘工具也出现在地图上——科学仪器的重要性增加之后,成为了一种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图像。最后一部分教授介绍了国际物品流动背后的地缘政治和社会学因素。他以一个中国制造的银壶为例,1686年暹罗使团访问法国时它被赠送给路易十四,法国也向暹罗回赠了国礼;彼时法国刚刚击败西班牙,热衷于与暹罗建立关系显然是与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地有地缘政治关系。此外还有一些本不应流动的物品,其流动到欧洲一般是因为殖民帝国发动的战争。这些物品并未详细登记造册,因此存在确认的难题。不过教授也提到,他对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与中国达成了一些文物电子化的合作感到高兴。在讨论部分,布尔东教授主要回应了两个问题。其一是中国商品在欧洲的情况。与中国商品相关联的基本都是精英阶层,而我们仅仅讨论了其中某些人;且效仿当时凡尔赛流行的趋势和真正喜欢中国风格是两个概念:在16至19世纪这一比较长时段之中,中国的形象发生变化,因此“中国风”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热”其实是西方对于东方幻想的一种投射。其二是关于欧洲工业革命之后带到中国的物品是否产生了与欧洲发生的“中国热”相对应的影响。他认为从欧洲向中国流动的物品基本都局限于宫廷,很少流动到民间。因此,国礼交换对人民的影响往往是微小的,它们背后往往是政治经济目的,就如同法国回赠给暹罗的礼物藏有传教目的那样。

24日上午第二场讲座,由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吴蕙仪围绕“清代中欧之间文本的旅行”这一主题展开。旅行史涵盖方方面面的主题,她的研究注重旅行史中的知识史维度,通过探究耶稣会士在华的知识获取途径以及当时欧洲对于中国知识的建构,来理解中欧两套不同知识系统的旅行与交流背后所反映的文化碰撞,为如何以平等的跨文化视野进行知识史研究提供了范式。首先,吴蕙仪指出明清时期是中国书籍市场发展的一个飞跃期,坊间印书不仅在数量上大大增加,在内容上也有了极大的丰富,除传统的儒家经典以外,还印刷了相当多的白话小说以及日用百科书。传教士从晚明开始进入中国,可以说是恰好踩在了明代中后期,也就是书籍印刷业大发展的时间点上,因此就有了几个问题,传教士究竟翻译和阅读过哪些中国文本呢?而这些文本又如何参与欧洲对于中国知识的建构?首先在对中国儒家经典文本的翻译上,吴蕙仪以1689年在巴黎出版的儒家四书的拉丁文译本为例,揭示了传教士们入华后近70年来对儒家四书陆续的翻译、整理、修改等工作,并指出传教士不是一个统一的团体,他们就翻译问题有过很多内部的争议,同时儒家经典在中国文化的内部解读也是非常多元的,中国内部不同著书,不同流派著书之间的分歧,有的时候可能会大过传教士的翻译所造成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影响这些文本所勾勒出的一个由儒家治国理念所统治的理想化的中国形象。接着在对非经典性文本的翻译上,吴蕙仪指出这些传教士涉猎广泛且经常选取书中有用的部分进行翻译并以注释的方式对其内容补充和批判,这些与翻译经典著作截然不同的翻译方式体现了传教士与非经典性文本之间一种开放的、平等对话的关系。在梳理完明清时期传教士对中国文本的翻译问题之后,吴蕙仪接着讨论了耶稣会翻译的中文文本在欧洲的接受情况。宗教因素在这之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一方面,对于同一文本的诠释往往在天主教欧洲以及新教欧洲有着天壤之别,以《豆棚闲话》为例,这本书原本是被耶稣会传教士翻译来抨击中国的无神论的,但传入英国后,英国的新教徒反过来用这本书嘲笑天主教世界的各种腐败与迷信如何比无神论更加罪大恶极。另一方面,许多天主教传教士翻译来的文本在欧洲的传播离不开新教世界,1685年《南特敕令》取消后,大批从法国流亡的新教徒在荷兰等周边地区建立了一个不受法国出版审查制度左右的境外法文出版业,一些原本在法国本土遭到禁止的出版物,如儒家四书等很快由这批人出版了法语的摘译本,这些法文摘译本也是孔子思想在欧洲传播的主要途径。最后,吴蕙仪总结说,通过研究这一时期欧洲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也会给中国一个全新的视角来更好地反观自我,审视自身传统内部的多样性。
9月25日上午,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克里斯蒂安·托巴洛夫(Christian Topalov)作了主题为“17至21世纪法国边界简史”的讲座。托巴洛夫教授将这一时间段法国边界的形成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法国在这三个阶段中逐渐与周边区域乃至整个世界接轨。托巴洛夫教授的研究补充了旅行史在国家维度上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国家权力如何影响历史上的旅行,并且托巴洛夫教授还指出在全球化的时代,随着各国对人员、思想的旅行的政策调整,旅行史不仅仅需要关注过去的问题,同样也要重视关于未来的问题。第一个阶段是物理意义上的边界,即划分主权国家疆域的边界的形成。这些边界起初由地理学家根据自然的山川河流划定,但这样的自然边界理论在实际应用时有两个主要问题,一方面,沿山川河流两边居住的村民往往共同使用这些自然资源并形成了当地的共同体,因此难以通过自然边界确定他们的归属,另一方面边界的形成中有很多不确定的人为因素,比如战争、外交谈判等都会造成边界的变动,因此实际上物理的边界往往需要通过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最终确定下来。第二阶段是区分法国人与外国人身份的文件边界的形成。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人就通过出生地还是血缘关系来界定法国国籍的合法性这一问题争论不休,最终1889年出台的法律规定以出生地来界定法国人的国籍,许多社会权利,如就业权也只有拥有法国国籍的人才优先享有。随后托巴洛夫教授还梳理了护照、身份证等快速鉴别个体身份和监控人员流动的证件在法国的发展史,并指出随着这些人为边界的形成,一套严格区分法国人与外国人的歧视性制度就诞生了。第三个阶段是由欧盟创建的边界。自1985年签订的《申根协定》开始,欧盟内部各国决定逐渐取消边境的审查,理论上而言法国的边界就是欧盟的边界,但随着2015年叙利亚战争爆发引发的非法移民、恐怖袭击问题以及近年来新冠病毒的爆发,许多申根国家都迫于现实情况以及国内右翼势力的压力开始临时性关闭边界,虽然仍然有许多非政府组织致力于救助难民,但这一欧盟边界实际上正处于分崩离析之中。作为“旅行”的对立面,托巴洛夫教授的研究为我们更好地了解法国的“边界”以及开放性与封闭性的互动提供了新的视野。

25日上午第二场讲座由普瓦捷大学的埃马纽埃尔·马蒙(Emmanuel Ma Mung)教授围绕“中国国家、侨民与新丝绸之路”这一主题进行。马蒙教授专注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的中国侨民,通过研究这一至关重要但却一定程度上被人们所忽略的群体,突出了人口的跨国旅行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马蒙教授首先分享了几类移民在法国的发展历程。第一类是劳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对劳动力的需求,法国吸收了十几万中国劳工来进行挖掘战壕、搬运弹药等工作,战争结束后,大部分劳工都被遣返回中国,只有约两三千人留下。第二类是来自浙江地区的小商贩,这些商贩起初主要来自浙江青田地区,在法国贩卖特产青田玉,随后和当地犹太人合作经商,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商业网络,他们帮助许多来法的中国人获取身份证件,而其在巴黎的聚集地也成为了中国移民的重要支点。第三类是留学生,这类人属于精英群体,他们内部各个团体持有的政治观点各不相同,并在学习工作之余参加了许多政治活动,这段经历对他们后来在中国的政治生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之后马蒙教授探讨了这些海外移民对中国的影响。首先在经济上,大部分中国移民都与国内家乡以汇款的方式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在中华民国以及新中国建立以后,大批华侨回国并进行投资,大大推动了诸如广东、福建等地的经济发展。其次,归国华侨对于中国的社会变革也起了一定影响,除了国外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与理念外,他们还将诸如让女性担任家庭商店中的管理者职位的生活习惯带回了中国,从而潜移默化地改善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许多学校建立的背后也有华侨的身影,这些行为都大大促进了社会进步。最后在政治上,中国近代社会的许多重大政治变革都先由海外华侨引领,他们遵循着一套先在海外形成政治思想,随后再传输回国内的政治活动模式,如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创办兴中会、同盟会推翻清朝统治,在法国留学时的邓小平、周恩来先生等人创立共产党支部等等。马蒙教授针对小众群体的分类研究,为学员们思考人口跨国旅行这一问题提供了微观层面的参考。
在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通过本次研讨班,来自中法两方的学者对旅行史的理论方法、实践路径与未来展望等方方面面展开了深入的交流。来自法国的这些宝贵的学术经验,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比较重要,旅行史方兴未艾,而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可以为法国学者提供新材料,中国的全球史研究也可以与法国的世界史研究展开对话和交流。本次研讨班丰富多元的议题揭示了历史上的旅行并非那般孤立。无论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逶迤连绵,还是近代航海探险的波澜壮阔,尽管面临自然与人文的重重挑战,人类始终保持着跨越地域、探索未知的强烈愿望与不懈动力,整个世界也正是在一次次旅行中悄然发生改变。
就旅行史自身研究的现实意义而言,在如今全球化的交融与碰撞下,各国之间物与思想的旅行日益频繁,这些旅行如何逐步发生?又如何通过考察历史上不同文化之间的相遇、冲突与融合来理解我们当前的全球化处境?历史学独特的视角、对于史料的深度挖掘以及中法学者合作下的广阔视野都能让历史学者为此进行细腻的分析,通过对旅行史的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深化我们对全球化乃至整个世界的理解。
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由华东师范大学、法国人文科学之家基金会、中国法国史研究会、浙江大学与法国巴黎第一大学于2004年创办,二十年来,中法学界跨越了疫情阻隔,以研讨班为平台展开交流对话,体现了双方学者着眼现实,不断在推进学术研究与文化交流层面所做的深度努力和尝试,同时也为国内师生学者了解国际学界前沿动态、丰富自身学术发展道路提供了平台与契机。今年7月3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与法国人文科学之家基金会、巴黎一大、浙江大学和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在法国共同主办了 “中法瑞历史文化研讨班20周年(2004-2024)——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回望了研讨班创立二十年以来的发展历程,就研讨班的主题、授课人员、运行及出版翻译等问题展开了研讨。

2024年7月巴黎研讨会与会学者合影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