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是关联的声音。”在格非新作《登春台》中,这句格言被选中,作为一家物联网高科技公司的标语。对于整部小说来说,它似乎也可以成为一种题解。除去序章和附记,剩下四章以四个人物名为题,就像他们在各自的房间。而原子化的布阵,是为关联启动设置的原点。上帝之手便是作者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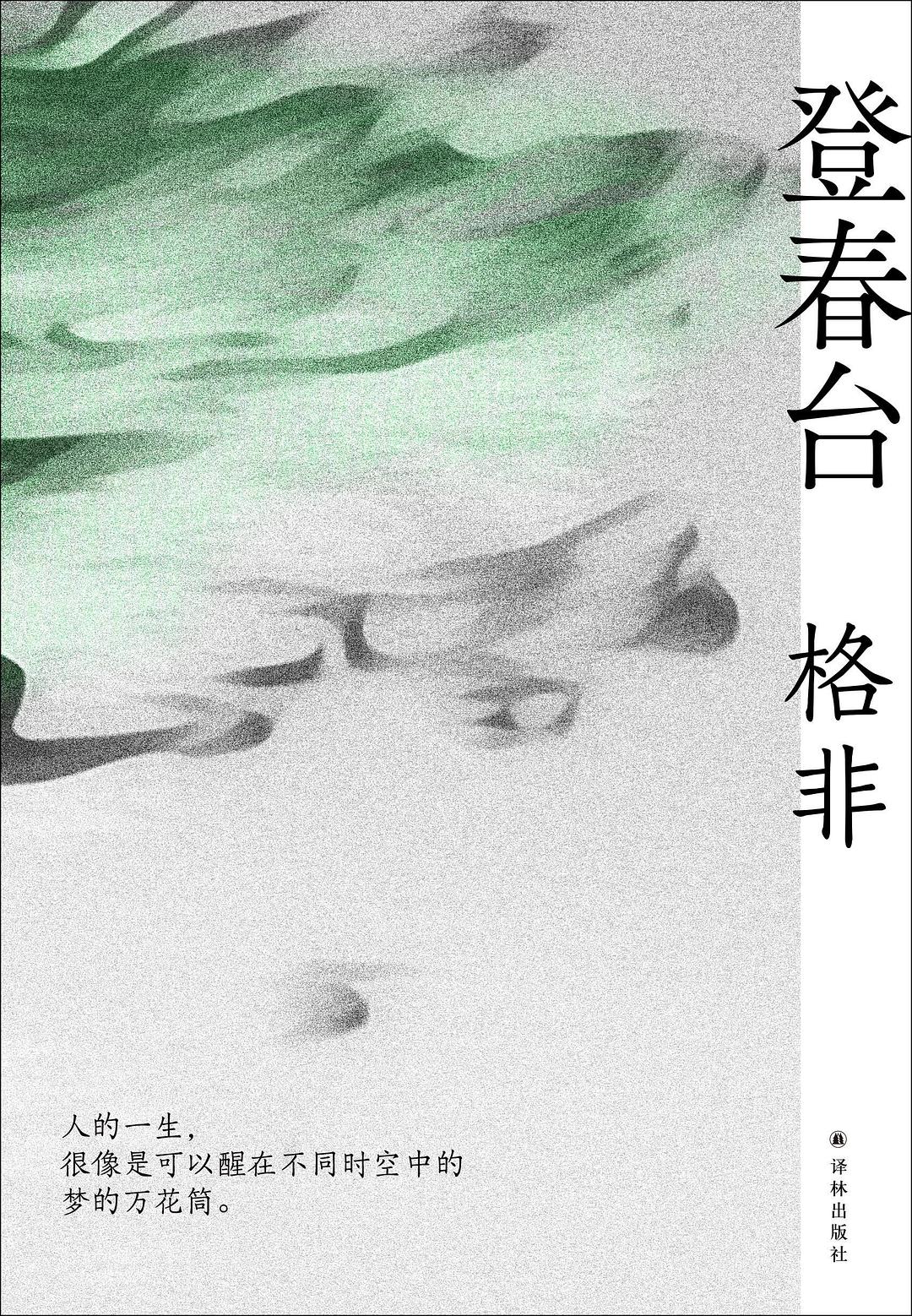
《登春台》书封
四个籍贯背景年龄各异的人物,围绕着物联网公司发生关联:沈辛夷是公司新员工;陈克明从助理变董事长;窦宝庆曾经是司机,他的工位留给了沈辛夷;周振遐是公司创始人。不过,作者首先赋予他们的,是人称的差异化和呼应关系:第一第四章,“她”/“他”。第二章,“我”。第三章,“你”。借马丁·布伯的说法,以事物为对象的活动,“是‘他’之国度的根基”,而“凡称述‘你’的人都不以事物为对象”。也就是说,人称迥异,意味着主客关系预设的区分。以此为参照,用第三人称指代的“沈辛夷”和“周振遐”,从出场开始,就被叙述者置入一个隔绝性的对象世界,在形式上服帖地匹配着他们拥有的单独的房间。
这样的隔绝却体现了保护作用。沈辛夷和周振遐都是厌烦人群的人,在更微观的层面上,他们惧怕“声音”。这种惧怕源于早年创伤:周振遐住过筒子楼里的小房间,“犹如在风暴中颠簸的小船”,从此心脏出现不可逆损伤。少女时期的性侵遭遇在沈辛夷体内烙下充满污秽感和攻击性的絮聒声,在那以后,别人的生活世界对她来说就是炼狱。孤立化、避世性的第三人称抚慰了他们过敏的神经,保障了他们听觉的安全,让他们有足够空间“以己为他”,只聆听自己的声响。
第二人称却好像为单独房间开的门,“你”字一出口,就是开门的声音。“陈克明”一章是第一人称,但“你”先于“我”出场:“你要是问我家在哪里……”。这个预设性的问题背后,是一个开朗的“我”。他主动向外部世界发起聊天邀请,甚至兴致勃勃地揣摩对方的好奇心,心甘情愿做一个随时响应听众要求的讲故事的人。“我-你”关系意味着共同在场并缔结纽带;依靠“陈克明”,读者获得了与文本之间的共时性。而在小说内部,陈克明这个庸俗、忠诚、好心的人物,正是他友善地冲击着沈辛夷和周振遐寂静的世界。同样,也依靠他,让“窦宝庆”的故事浮出水面。
拥有第二人称的“窦宝庆”,在小说里,是一篇人物报道,经由记者小罗,来到陈克明手中。窦宝庆是全书在空间维度最幽深的人,他身处房间里的房间,当我们遇见他时,他已经退出一般社会生活的舞台。他难以在场了。正因为如此,对他使用第二人称,堪称一次抢救般的召唤和释放。也正因为如此,似乎再一次验证了格非寄寓在人称实验中的某种伦理用意。这也是阅读过程带给我的强烈体会:人物得到了作者参差有致的善待。整部小说包含了一种巨大的善意。“你既是在这世上苦熬并艰辛过活的一个人,也是所有的人。”小说里,所有人生活的深处都包藏着一点苦难,这苦难制约着他们的生命。而来自作者的善待,并不表现在对人物命运的弥补。相反,他维持着苦难本身的生命力,让它在特定时刻流淌出来,浸润人们的梦境与喉咙,向外漫溯。
由于杀人往事的曝露,窦宝庆逃亡并被捕。不过,他好像并不抗拒这一结局的到来。他的反应更像是顺应命运的安排,在悠远而黢黑的公路上走完最后一小段路。押解途中,他被车窗隔离的人流簇拥着。他开始注视和揣测他们,渐渐理解这个原本“无法理解的世界”。最后,在监房里,他获得了“发现自己在退烧的那种清凉”。事实上,他是主动坦白罪行的,以讲故事的方式。“讲故事”本是窦宝庆和郑元春之间催动激情的方式。描述一桩激烈的性犯罪,对情人来说无异于一剂春药。窦宝庆讲了好多遍。在故事里,无名的女孩被无名的男人强暴。讲这样的故事,对他来说如此轻松,“故事本身就能自动讲下去,你跟着它往前走就行”。因为,在所有这些故事背后,只有唯一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个把“你”变成杀人犯的故事。最终窦宝庆把情色场景转化为告解场景,向郑元春奉献出那个真正的故事。或者说,是那个故事自行跃出,引领他终结自己悬浮的生涯。

作者格非
“讲故事”让窦宝庆拥有听众,不再单独保有自己的内心。他由此临时地摆脱了离群索居的境遇;也是从这一刻起,那些被他刻意疏远的环境和人事,重新清晰起来。窦宝庆是四个人物中间唯一没有梦境的人。这或许因为,在杀人以后,他的生活本身就成了一个梦。而对于其他三人来说,梦境是重要的。梦境承担着和“讲故事”类似的功能。本雅明谈到心理分析和故事的相悖关系:“讲故事者越是自然地放弃心理层面的幽冥,故事就越能占据听者的记忆,越能充分与听者的经验融为一体。”也就是说,心理分析让经验保守在个体内部,同时告诫着经验边界的不可逾越。“梦境”原本作为一种典型的心理成像手法,不过,在《登春台》中,却能观察到“非幽冥”的用法。不但不够幽冥,反而一再意指清晰地为梦境主人的现实问题伸张。沈辛夷的梦境指向她幼年时对母亲婚外情事的含混记忆。借由梦境,一段过往突然向她敞开,“它足以解释自己与母亲之间那种仿佛与生俱来的冷漠与隔膜”。陈克明在梦里与他牵肠挂肚的前妻静熹相遇。他像过去无数次那样,跟她商量一件工作中真实发生的庸俗小事。这个哲学家般的女人,再一次给出了冷静妥当的建议。南柯一梦,幻影消散,陈克明失落地哭湿了枕巾。但换个角度讲,他以一种非常现实的方式储存了幻影。那种迫切保留的愿望,让他始终拥有着大于单数的内心。小说人物在梦境中完成的,是对局部过去的重新诠释。就像讲故事一样,做梦意味着尝试把握自己生命难题的话语权,也意味着向那些令人恐惧、忧愁和留恋的他人靠近。
周振遐的梦关乎少年时代的砖窑、竹林、田野和寺庙。事实上,这个梦仿佛来自格非自己的某段写作“前世”。在这个意义上,宣告周振遐的梦醒,就像提醒读者移步换景,进入当下的作者语法。“而现在,他的梦就要醒了。”小说中,这句话单独成段,以一种毫无疑问的时态标志,将“现在”充分前景化。如果把“关联”假设为小说对现时性特征的分辨,那么,回避或开辟“关联”,则体现了小说对“现时”的抵抗和再生产。“关联”对于个人而言,可以是伤害,鉴于它常常牵及无法避免的外部入侵;但“关联”同样事关生活的核心诱惑。《登春台》既保卫壁垒也撞击壁垒,在熙熙攘攘间庇护生命的厌倦与期盼。
(本文作者罗萌,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