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黟县宏村镇塔川村风光。视觉中国 资料图
在山村里,金大爷让我们看家谱。一边翻看家乘之页,一边听他讲述祖上的和现时的事。我们听着,拍着照,感受这特别的缘分。
这里是皖南。山溪蜿蜒而下,在村子正中的大树下喘了口气,留下一片气韵不凡的金色河沟。
山溪接着游动,到了低洼的村边,水量渐大,有人在溪水里摸鱼。摸鱼人告诉我们,这溪水汇入下一条河流,最终投入长江的怀抱。河流沿途有炊烟四起,有歌声响起,带着无尽的诗意。
金色河沟边,便是金大爷家。
我们随性走到金大爷家门口时,他们一家正在吃午饭。我们说明参观之意,一家人热情地带着我们看屋宇,看旧时物事。告别之际,金大爷送出门来,浅聊再三。也许是大山里的神话传说太精彩,抑或我们的探寻颇显真诚,勾起了他的展示欲,他想了想,问:“我有家谱,看不看?”
这话让我既惊喜,又失落。在南京,我的家中,并没有家谱传世。
金大爷的家谱,追溯到后唐,尤其在有明一代枝蔓横生,充满了传奇意味。在历史的烟云中,普通人物的颠沛并不稀奇,但在离乱中把家谱好生护佑,形成一套完备的体系,令人惊叹。
有了家谱,一代代人就有了来来去去的“线索”和“站点”,就不会迷茫。
他们家族不仅有家谱,在村里还有一座祠堂。祠堂是明朝建筑,土木浩大。每逢重大时间节点,这里有仪式举行,不知道跳了多少代的舞蹈在山风里荡漾。这些活动,还是源于家谱的力量。围绕一部家谱,人人各司其职,遵守血脉秩序,在时光深处完成一份传承。
这让我大为羡慕。
我在家族里也算是有辈分的人,“厚德载福”中的“载”便是我的专属。但我家的辈分,是残缺的,“到此为止”的,透着一股凉意。这套辈分系统,往上不过知晓三层,往下已无延续。多年前,父亲还年轻,他见到过家中传下来的家谱,可惜它很快消失无影。根据若有若无的线索,他多次搜寻过,无果,引为憾事。
我曾使用过长辈们给我起的名字——“刘载量”,作为笔名,但这个名字并没有在正式场合登记过,连曾用名都算不上。我在用这个名字的时候,虽没有增加什么灵感,但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喜悦和亲近感。仿佛这个名字经由了祖辈的摩挲和祝福,是一种不可浪费的资源。
父亲已经七十多岁,“寻根”越发成为他的愿望,他很想知道“我是谁”。过龙年春节时,他听我堂叔说,广东某地有刘氏家谱,起意去看。但杂事缠绕,至今未能成行。
其实,即便见了所谓的家谱,怕也很难接续上。但也不能否认,一个见了家谱的人,可能有一份了然于胸、似曾相识的情绪萌生,甚至托举起一个人对家族历史的联想和遥望。
我不知道,这份寻觅究竟有多大的意义,但是一个人被失去家谱的遗憾久久地缠绕心灵,带来的一种痛感,却是分外真实的。
有人对这种探寻的努力不以为然,认为活好自己这一辈就行。这当然是一种洒脱的人生态度。
不过,我们明明看见了一条山溪的金色河沟,明明被它的精确流向所吸引,明明知道它向何处去,进入何方领域,却无法更进一步,去山巅查看源头,去和兄弟姐妹们一起感受那些神秘色彩和特定的由来,人生况味终究少了几许。
人生在世,都是在哭笑后远去,满足也好,不满足也罢,都可谓精彩。但谁又能说,我们的“来时”,就一定无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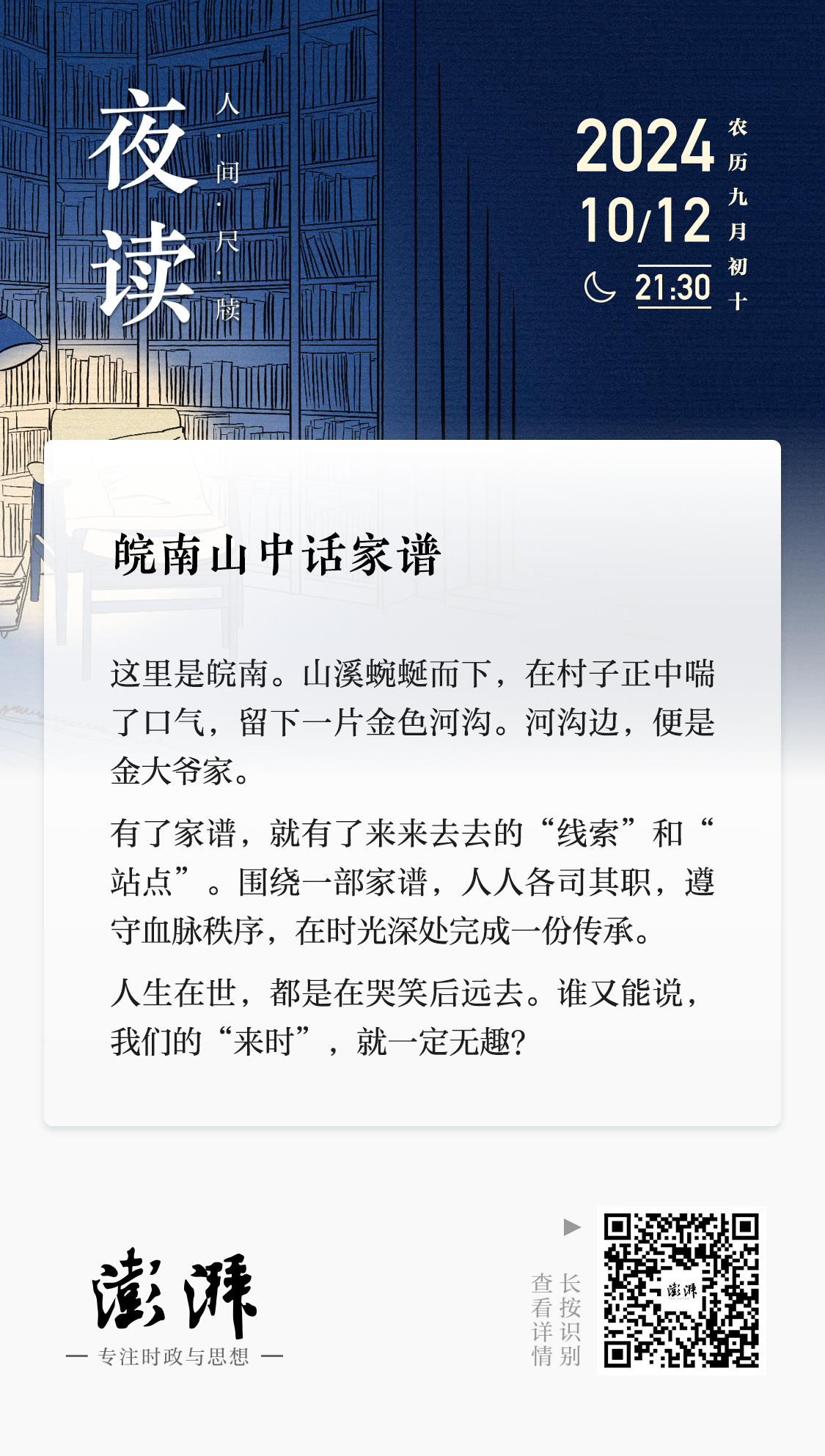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