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是谈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避不开的一个名字,而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史所依存的重要坐标。两者之间的联系也十分奇妙:丁玲一生几次投向上海,作家丁玲在这里登场,几部小说集引得1920年代末的上海万人空巷;革命者丁玲在此处发轫,参加“左联”,主编《北斗》,1932年入党。我们所熟悉的丁玲的历史,从上海开始大踏步走来。那么在丁玲成为“丁玲”之前呢?从湖南出发,第一个塑造她的城市,就是上海。今天走在上海的街道上,还能看见承载着冰之成为“丁玲”之前记忆的旧地。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摄于1925年
1922,平民女子学校: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
1922年2月,丁玲跟着王剑虹从长沙抵达上海,读共产党办的平民女子学校,这年她十八岁。这时候她带着从湖南带来的名字“蒋玮”,还有在家里使用的小名“冰之”。到了平民女子学校,她抛掉了蒋姓,变成了“冰之”。姓氏——一个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榫卯——的消失,似乎是迈向现代的某种标志。但是,“废姓引起很多麻烦,只好随便加了一个姓”,于是迈入上海都市的是丁冰之。
而丁玲这个最终代表她的名字,是1926年春“为去上海想当电影演员”,她同朋友在字典上盲眼乱摸到的字而起的。1927年投稿《梦珂》,她又用了这个名字,于是一直用了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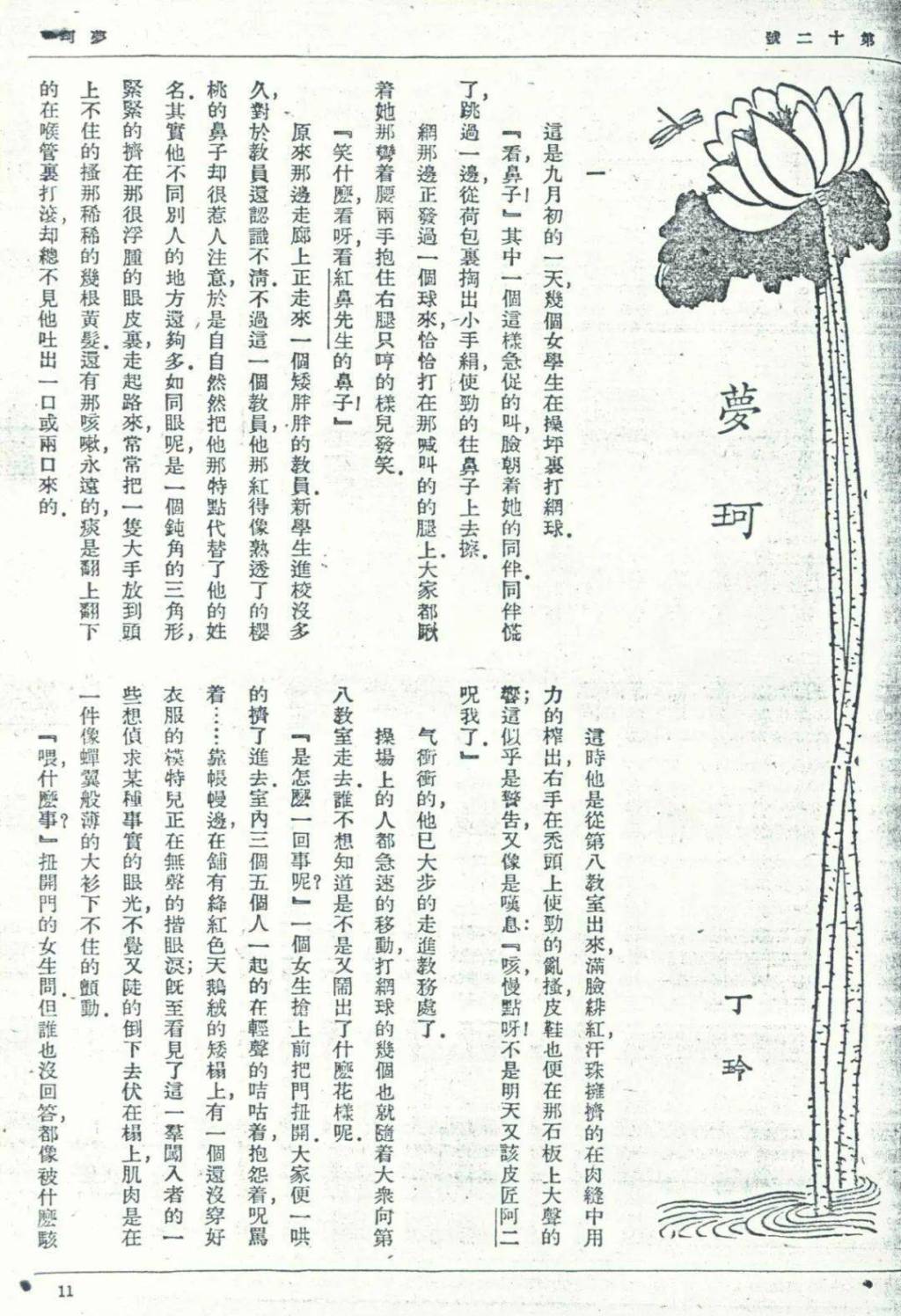
《梦珂》发表在《小说月报》上
来到上海之前,她相继在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周南女子中学和岳云中学学习,又相继舍弃,渴望来上海“学最切实用的学问”。丁玲在黄浦江边的码头上踌躇满志地眺望着往来的人群的时候,心里浮现的大概是五四式的现代图景。共产党刚刚创立的平民女子学校在等待着她,还有其余二三十个学生,其中有的还是文盲,要从识字开始学起。
她像过去一样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社会活动。学校主要教授的是妇女运动,这和她过去从母亲及向警予那里接受的思想非常契合。她跟着共产党员张秋人去浦东纱厂演讲,在街上为罢工的女工募捐,同时对马克思诞辰纪念会、无政府主义者的会议等等也满怀好奇。女学生丁玲拼命地张望着,试图将寄居在上海这座城市中的复杂知识尽收眼底。
但最初的新鲜劲过去之后,失望是很明显的。这所学校的学生素质参差不齐,而教学方面的问题则更为严重。没有固定的教员、教材和教学计划,老师大多是兼职,有时学生们得夜里从床上爬起来听课,因为老师刚好来了。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和茅盾,这些名人的课都不使她感兴趣,或是早已学过。她还和王剑虹等人怀着“朝圣的心情”去民厚里拜访自己最为崇拜的郭沫若,而后大失所望。丁玲在1978年的日记中还记录过这件事:“当我们在民厚里外边马路上等电车的时候,确实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懊丧。”
到了暑假,丁玲就和王剑虹一起退了学,开始了每天读书自学的生活。她特别爱读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或是刊登在《小说月报》上的俄国小说。在这座有名的“且介”之城中阅读外国小说,类似某种有趣的互文与对抗。生活在上海,丁玲可以便利地、同时同步地买到世界上新出版的流行的文学文化刊物,跨界的语言和文化的混杂性直接来源于自身的文化生活空间当中。然而,丁玲又越过了当下的流行文化,苦读19世纪的俄苏文学,在异质的文化空间中悬置自己本土化的迷思。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回望自己的创作生涯,提到的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这些人,“直到现在,这些人的东西在我印象中还是比较深”。
和她一起从湖南来到上海的女伴里面,王一知当年就加入了共产党,而丁玲和王剑虹则远在共产党人的圈子之外。在1922年百家争鸣的混乱时代里,共产主义和刚刚草创的中国共产党实在是力量弱声量小的一支,他们所宣讲的内容也并不让人十分满意。对于年轻的女学生来说,他们来去匆匆,十分忙碌,而鱼龙混杂的班子里某些浮夸的投机分子则使人厌恶。她们俩崇尚自由,尚不愿被管束,未来的人生道路还在一片朦胧的迷雾之中。到了秋天,她们就结伴离开了上海。

丁玲与王剑虹(右)
1923,上海大学:闸北青岛路青云坊
丁玲第二次来到上海则是由于瞿秋白的建议。1923年8月,丁玲和王剑虹第一次见到瞿秋白,是在南京,共青团二大的时候。从俄国文学开始的谈话非常投机,最后瞿秋白建议她们去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并保证在那里可以自由选择。于是丁玲又回到了上海,在中文系当一年级的旁听生。或许就是由于这段经历,莎菲女士进入我们的目光中时也是一个旁听生。丁玲又进入了茅盾的课堂,迷恋上他讲述的离奇美丽的希腊神话,同时听社会学系的课,崇拜因发表《非孝》而颇有名望的施存统。不过,她心中最好的教员还是瞿秋白,他既博学又浪漫,和她们畅谈文艺复兴、唐诗宋词和普希金。
贯穿丁玲一生的傲气极早显露。她在上海大学期间落落寡合,1924年春天,她和剑虹常常设法买三元五角一张的包厢票,坐在油头粉面的时髦太太、姨太太们中间,“满不在乎地”欣赏正处盛年的梅兰芳演出的《洛神》《霸王别姬》《游园惊梦》。施蛰存在五十多年后写了《丁玲的“傲气”》来怀念这位当年在田汉的西洋诗课堂上坐在教室前排的女同学,又在1979年和1989年各写一首诗以怀丁玲。1982年,丁玲将自己的新作寄给他,扉页上写着“施蛰存同学指正”。
1924年初的冬天,瞿秋白与王剑虹结婚。学校搬迁到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丁玲与瞿秋白一家、施存统一家及瞿秋白之弟瞿云白一同住到学校附近慕尔鸣路的一所房子里。瞿秋白夫妇依然同丁玲很亲近,他们总是在丁玲的屋子里,围着煤油炉,三人一同吹箫、唱昆曲。然而丁玲还是一天天寂寞下来,当初和她一起站在上海码头上眺望着,一起在这个大都市里冒险的剑虹毕竟是不再为她所有了。她望着煤油炉亮光的记忆,被不断地氤氲到后来的创作中去。1930年完成的《韦护》,就取材于此时在她身边欢笑的这对夫妇。更早的1928年,青年丁玲的成名之作《莎菲女士的日记》,那个莎菲不断写信的模糊客体,某种遥远乌托邦的化身,归依家庭而与莎菲分别,最终撒手人寰,指向莎菲日记终结的蕴姊,正是坐在她身旁的王剑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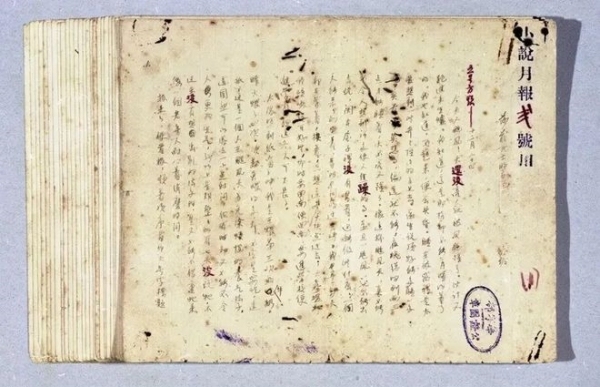
《莎菲女士的日记》手稿
1924,慕尔鸣路
1917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修完一路,命名为慕尔鸣路(Moulmein Road)。1924年,丁玲还不满二十岁,在这座以异邦城市命名的街道上,她和瞿秋白与王剑虹一同望着关了灯的房间里煤油炉在天花板上留下的“闪烁的微明的晃动的花的光圈”。瞿秋白后来说:“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这句对丁玲一生的判语,在这些朦胧而晕散的光圈中已然成型。1980年,76岁的丁玲写下《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青年男女围着煤油炉谈笑欣赏火光的往事,三人之间微妙难言的气氛,五十多年后犹在眼前,脉脉分明。慕尔鸣路早已更名为茂名北路,旧屋不存,斯人已逝。剑虹1924年夏天即因肺病而亡,丁玲从湘返沪扶棺,秋白在十一年后于南方游击战争中被捕就义,丁玲此时被国民党囚于南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如此冷漠、可怖。如淅沥冷水般的日子,握于半个世纪后的《魍魉世界》。煤油炉投在天花板上的温暖光焰这般虚幻,青春良辰逝如流水。
1924年暑假,丁玲和向警予谈话后向瞿秋白夫妇辞行,打算回湖南看望母亲,尔后前往北京继续求学。这对他们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在丁玲离开上海的那个晚上,只有瞿云白提着一篓水果送她上船。她最后打量了一下这座城市,“这时已是深夜,水一样的凉风在静静的马路上漂漾,我的心也随风流荡:上海的生涯就这样默默地结束了……”
实际上,离开上海仅仅一个多月以后,丁玲就因剑虹堂妹发来的电报打包行李匆匆返回。她带着“惶惶不安”的心情,回到了她寄居了半年的慕尔鸣路住所,迎接她的是“人去楼空”——剑虹的棺木已经移放到四川会馆,而瞿秋白也奔赴广州参加会议,只有剑虹的两个堂妹和瞿云白沉默相迎。瞿秋白把当初丁玲送赠他的剑虹的照片包在白绸布里返还了,照片背后还有他当初写下的诗,第一句是:“你的魂儿我的心”。魂儿是丁玲对剑虹的称呼,她总是用“虹”来唤这位好友,瞿秋白笑道应该是“魂”,而他总是唤剑虹为梦可,这是法语的“心”的意思。三年后,丁玲在北京的公寓里写作自己的处女作《梦珂》的时候,是把她的魂儿放进去了。她在冷清的四川会馆流下了“如泉的泪水”,作为冰之的最后一场泪水。她很快与剑虹的堂妹一同乘船北上,背后起伏的城市天际线,留下了丁玲成为“丁玲”之前的模样。冰之即将抵达北京,一个知识分子的丁玲和一个革命者的丁玲,都在那儿等待着她,而后一同被丁玲带回这个城市:上海。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