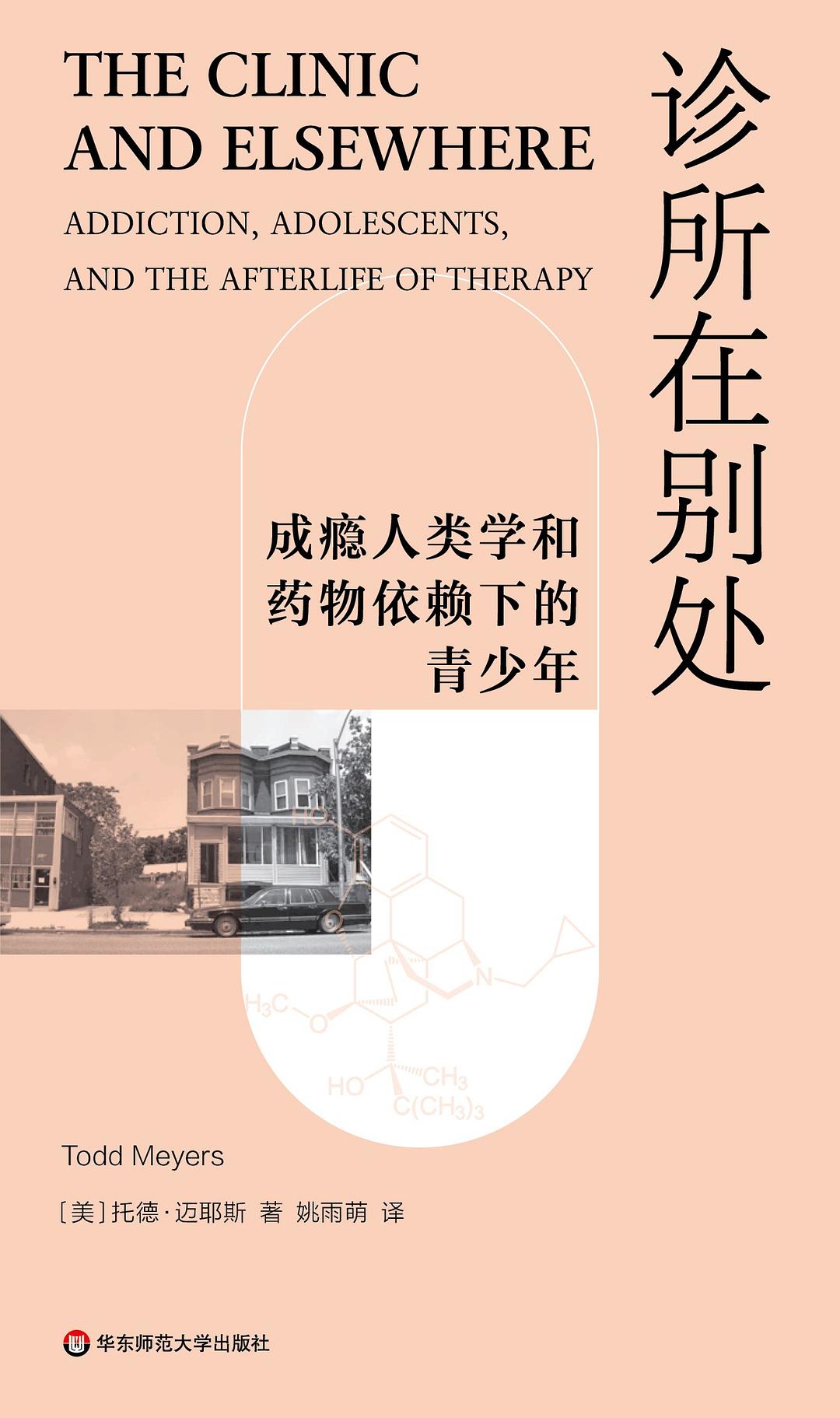
《诊所在别处:成瘾人类学和药物依赖下的青少年》[美]托德·迈耶斯著,姚雨萌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2024年5月出版,248页,55.00元
美国药物滥用正在撕裂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包括他们的家庭、社区和友谊。近年来,新的药物疗法既带来了康复的新希望,也引发了对药物滥用的担忧。当走出诊所后,这些青少年药物成瘾者的生活将被如何重塑?药物依赖的“治愈”的可能性在哪?美国人类学家托德·迈耶斯(Todd Meyers)在三年时间内追踪了巴尔的摩不同身份背景的青少年接受药物治疗的经历,尝试重新讨论药物依赖,以及这种成瘾的生活经历如何超越了对于药物治疗“成功”和“失败”的二元分类,从而开启关于生命和健康的哲学对话。
托德·迈耶斯目前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社会医学研究的玛乔丽·布朗夫曼讲席教授,在医学院和人类学系教授课程,他的教育背景有些“跨界”,曾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接受人类学和公共卫生科学的训练,并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学习艺术。他著有《一切都不是她》(All That Was Not Her,2022)、《慢性病纪事》(Chroniques de la maladie chronique,2017)和《诊所在别处:成瘾人类学和药物依赖下的青少年》(The Clinic and Elsewhere: Addiction, Adolescents, and the Afterlife of Therapy,2013)等著作。
迈耶斯的研究涵盖社会研究和医学史、临床民族志,他还通过人类学方法研究视觉文化。他即将出版的新书《消逝 消逝》(Gone Gone,2025)追踪了发生在蒙特利尔的、因致命过量吸毒而产生的悲痛漩涡。他目前正致力于一项长期研究,探讨美国农村的精神疾病和仇恨暴力的医学化,该项目名为“我们之间的罪”(The Sin Between Us)。此外,他还在写一本创伤视觉文化的书,题为《未来创伤的形态》(The Shape of Future Wounds)。
《上海书评》邀请本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博士候选人姚雨萌就成瘾病患与医疗体系的关系、如何对待田野中的疾痛叙事等问题采访了迈耶斯教授。

托德·迈耶斯 (章静 绘)
关于研究对象,书中有一句话很有意思“青少年就算不嗑药也很让人头疼。” 青少年和成瘾二者本身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您研究的初衷是青少年问题还是成瘾问题?为何形成最后的研究议题?
托德·迈耶斯:我起初便关注成瘾与青春的交叠。年轻人戒毒的经历尤其复杂,他们被视为极其易受毒品的影响的一群人,而这往往言过其实。通过观察青春期与成瘾的相互作用,我看到了这些话题是如何彼此放大的。但在书中,我想努力提醒大家的一点是:归根到底,他们还是孩子。人们常常认为毒品剥夺了孩子的童年,但书里的这些孩子——无论我们称之为少年、年轻人,还是青少年——归根到底还是孩子……他们成长,他们改变,他们学习,他们犯错——凡此种种,皆是青春的模样。
巴尔的摩似乎是割裂严重的城市,正如书中的描述 “两头都能找到行家(德高望重的研究者和深受社会问题困扰的人)。”在进行田野调查过程中,您如何确定巴尔的摩作为研究地点,又是如何展开的?
托德·迈耶斯:我启动这项研究的时候,就已经住在巴尔的摩了,那时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不需要长途奔波,我在此就能找到回应研究的问题。
在巴尔的摩开展研究挺复杂的。一方面,巴尔的摩也太“过度研究”了。这座城市里的贫困和苦痛,因种族主义和结构性不平等而雪上加霜,但不管是好是坏,都吸引了大量研究者。有些时候巴尔的摩被称为“实验室”,这个态度蛮消极的。
另一方面,尽管问题重重,城市里也有大量的研究和医疗中心。从一开始,我就想了解年轻人在这些体制中的经历,包括研究体制,以及他们称之为家的地方。仅仅研究人们在机构中的生活(如诊所、医院、学校、监狱)是不够的,他们的世界还包括厨房和客厅。我想知道年轻人在机构和家之间的生活是怎样的。
书中有很多与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的对话,尤其是对个体的关注,似乎也影响到您后续的其他研究。但非专业的读者可能对此比较陌生,能否简要介绍一下康吉莱姆对您研究的影响?
托德·迈耶斯:乔治·康吉莱姆(1904-1995)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法国哲学家和医生,他最著名的可能是《正常与病态》(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1943)以及他对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指导。
要理解康吉莱姆对我这本书乃至我所有写作的重要性,最好的方式是了解他对个体创造规范的坚持。无论生病还是健康,个体都不断地协调与周遭世界的关系。康吉莱姆的思想深受德国神经精神病学家库尔特·戈尔茨坦(Kurt Goldstein)和美国生理学家沃尔特·坎农(Walter Cannon)的影响,这一点我在与历史学家斯特凡诺斯·杰鲁拉诺斯(Stefanos Geroulanos)共同撰写的书《灾难时代的人体》(The Human Body in the Age of Catastrophe,2018)中也有提及。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康吉莱姆帮我避免将研究对象简单归类到由文化建构出的笼统分类里:“成瘾者”或“病人”,而是更仔细地观察个体如何在这些分类之下日复一日地生活。
您反复提到了康吉莱姆的一句话:“学习疗愈就是了解今天的希望和最终的溃败之间的矛盾——却不拒绝今天的希望。”《照护的逻辑》一书中的照护也是给予希望,并在道德实践中修修补补。您怎么看疗愈教育与照护之间的关系?
托德·迈耶斯:我非常喜欢康吉莱姆的这句话。它强调了我们生命的有限,这是作为人类有机体必然面临的失败,因为到头来,我们都是凡人,而人终有一死。但这并不是用虚无主义或失败主义的视角来看待生命。
这句话对于成瘾医学以及照护挣扎在毒瘾中的人有着深刻的启示。即使面对失败,仍然保有希望,这正是照护的本质所在。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明天会怎样,因此也不应假设我们能预见他人的明天,这本身就是一个道义责任。当乔治·康吉莱姆谈到疗愈教育的时候,他在同时提醒医生和病人,今天的希望有其价值,无论未来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
书中改写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话“在疾病中,语言就会枯竭”。反思了民族志研究中过度使用疾痛叙事的技法,重点不是说了什么,而是如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所强调的那样,言说创造了“身体过程和文化范畴之间,经验和意义之间的辩证关系”。但在疾病与苦痛的民族志研究中,我们时常陷入患者的言说本身,这对人类学研究者也是很重要的提醒,能否就此展开谈一谈?
托德·迈耶斯: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仅对于医学人类学来说如此,对更广泛的医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而言亦是如此。我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疾痛叙事”的强调使得研究者倾向于将话语视为原始数据,如果有人谈到他们的疾痛体验,就被当作可以直接汇报的事实。但这样做忽略了说话时周围的一切,也假设了言说总是事实的集合。精神分析学家不会同意这种看法。我在研究过程中,试图像关注言语一样关注动作、情绪和沉默。弗吉尼亚·伍尔夫说得对,在疾病中,语言就会枯竭,但不仅仅是对于说话者,对于那些本愿倾听的人来说也是一样。当疾痛、戒断或疼痛的体验无法让聆听者理解,或不符合正确的叙事时,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重要。
相比于在言说上做文章,捕捉民族志研究工作中的手势、情绪甚至沉默并不容易,也更暧昧不明。您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遇到了怎样的挑战?
托德·迈耶斯:你说得对,这正是民族志研究的困难所在,但也是直接与人接触、而不仅仅是问一系列调查问题所能带来的不同。我不仅在诊所里反反复复地花时间与他们相处、交谈,还跟着来到他们的家中和社区,进入他们日常生活的世界。我在诊所内外与同样的人建立关系,观察他们在这两种环境中的相似与不同,或者在诊所外的各种不同环境中的变化。这事关我将注意力放在哪里。我不仅关注人们说了什么,还关注他们如何说的,他们似乎想回避的是什么,他们有怎样的行为,以及在什么情境下他们改变行动。这大概是作为民族志研究者对自己感受的笃信,并将其记录下来。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取决于作为研究者重点关注哪里。
您在写到戒断期的身体反应时,用了很长的篇幅描述生于爱尔兰的英国画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画作《床上人物的三张习作(Three Studies of Figures on Beds),1972》,这位追求“临床学”绘画的艺术家用“最完全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展现了语言所不能表述的感受。能否请您谈一谈在民族志中引入艺术作品的处理方式,以及这是不是有意摆脱疾痛叙事的尝试?
托德·迈耶斯:我非常高兴你问关于弗朗西斯·培根的艺术作品,我可以说上好几个小时。在我还是青少年的时候,他的画作就对我非常重要,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不过我现在看它们的方式已经大不相同了。尽管他的作品满是夸张与怪诞的躯体,如今我看到的却是他试图控制混乱。在书中,培根的《床上人物的三张习作(1972)》为戒毒过程提供了一种视觉语言。这些画作完美地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它们没有替代言说,而是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并承载某种特定的体验,倒不是说要取代那样的体验,而是找到与其产生共鸣的某种东西。

弗朗西斯·培根《床上人物的三张习作,1972》(francis-bacon.com)
读者们或许会对您的个人经历比较好奇,您从画家转变为人类学者,个人生命经验也会改变民族志的呈现方式,正如您说弗朗西斯·培根的作品对您影响很大,可以跟读者分享一下其中的细节吗?
托德·迈耶斯:我认为你的问题谈到了我为何以及如何试图摆脱对“疾痛叙事”依赖的关键。早在听说民族志之前,我在艺术学院学习绘画。弗朗西斯·培根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对人体的狂野且近乎恐怖的表现,但同时他也是一位尽职尽责的肖像画家。那些肖像画,时而俏皮,时而丑陋,他在努力探索如何表现他所了解的人的各个维度。我觉得我的民族志方法与此类似。我的民族志肖像充满了光影、人物与抽象,并尝试将我所见到的人物及周遭世界融入其中,尽管可能并不完整。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对弗兰西斯·培根绘画的讨论中提到“使暗面像人物图像一样呈现出来(make shadows as present as the Figure)” 您在第六章结尾提到了人类学研究中也有值得进一步解读的暗面,但并没有继续讨论下去,能否在此展开说一说?
托德·迈耶斯:弗朗西斯·培根笔下的人物形象狂野而扭曲,但正如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在关于培根作品的精彩著作《感觉的逻辑》中指出的那样,这些人物形象常常在床上、摔跤场中,或是一个盒子的轮廓内。“既狂野又受限”是培根绘画中看似矛盾的特征。但在目睹培根的画作后,会有种挥之不去的感觉,一种难以摆脱的印象。也许所有的一切在相遇瞬间就没有了意义,又或者因着这次相遇,所有的事物都映入眼帘。无论如何,那些不切实际、难以名状的感受和印象,依然存在并产生影响。我最近的两本书,《一切都不是她》(All That Was Not Her,2022)讲述了巴尔的摩一位女性长达二十年的生死故事,以及最新的那本《消逝 消逝》(Gone Gone, 2025)探讨了吸毒过量致死后的哀伤,试图在人类学研究投下的暗面中,为培根画作所传达的狂野与约束感创造空间。
研究一方面依托机构得以展开,另一方面又花大量的时间追踪青少年离开机构之后在别处不同的生活。在机构进行田野调查时,有哪些伦理上的困难与压力? 您如何看待人类学研究和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
托德·迈耶斯:这是个好的问题,也是研究人员不够关心的问题。首先,我问的是谁的问题?或许我认为找到了自己想问的问题,但很容易变作只是重申戒毒中心或医学上的价值观和重点。机构有其对好坏的一套看法。而我想了解的是这些年轻人自己的想法,而不仅仅是机构对他们的看法。这就是我追踪青少年走出诊所、回到他们家中和社区的主要原因。我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去摆脱让我们得以接触研究对象的机构。但对我来说,这样的时间和脆弱性正是一种伦理承诺的表现,就是要站在青少年的世界里,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看待自身。
离开机构之后的田野工作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也与成瘾研究的特点,请问您怎么看民族志研究中的模糊与断裂?
托德·迈耶斯:断裂是我追踪青少年戒毒治疗过程的特征,也是我的研究带给读者的启示之一。接受戒毒治疗的青少年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的生活也非静止不变。当他们结束住院戒毒治疗后,我会与他们失去联络,但当我重新联系上他们后,又会再度失联。这正是他们在家和机构之间进进出出的生活特征。断裂并不是研究的局限,而是这些青少年朝不保夕的生活经历直接导致的结果,我试着用文字记录下来,希望能让读者看见。
虽然巴尔的摩是一个研究型城市,但受访者似乎只认可并熟悉临床研究,而认为对社会生活的关注“称不上真正的研究。” 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矛盾?今天,当药物滥用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时,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托德·迈耶斯: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对成瘾和治疗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仅在北美,全球范围内都是如此。阿片类药物危机是促成这一变化的重要原因。但我们也早该改变看待物质滥用者的方式了。你说得对,如今成瘾和治疗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所以现在的工作是继续寻找新方法,以不同的方式来想象和讨论成瘾问题。毒瘾和治疗不再是孤立的研究问题,而是需要我们共同参与的话题,毕竟我们共享同一个世界。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却是我们都可以做到的事。即使我们认识到成瘾问题,往往是毁掉生活的社会问题与个人问题,我们也可以开始用不同的方式来谈论毒品使用和毒品依赖,而不再将这种行为绝对化。当我听到其他研究人员使用“瘾君子”这个词时,都不由得眉头一皱。有些人使用毒品,但并不符合毒品依赖或成瘾的标准;也有些人因使用毒品而导致生活分崩离析。但这些人同时也是姐妹、父亲、同事和邻居。他们的身份并不只是被毒品定义。因此,即便是术语上微小但有意义的变化,从“瘾君子”到“毒品使用者”的转换,也能够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那些使用毒品、并有时与毒品抗争的人——这或许也能让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