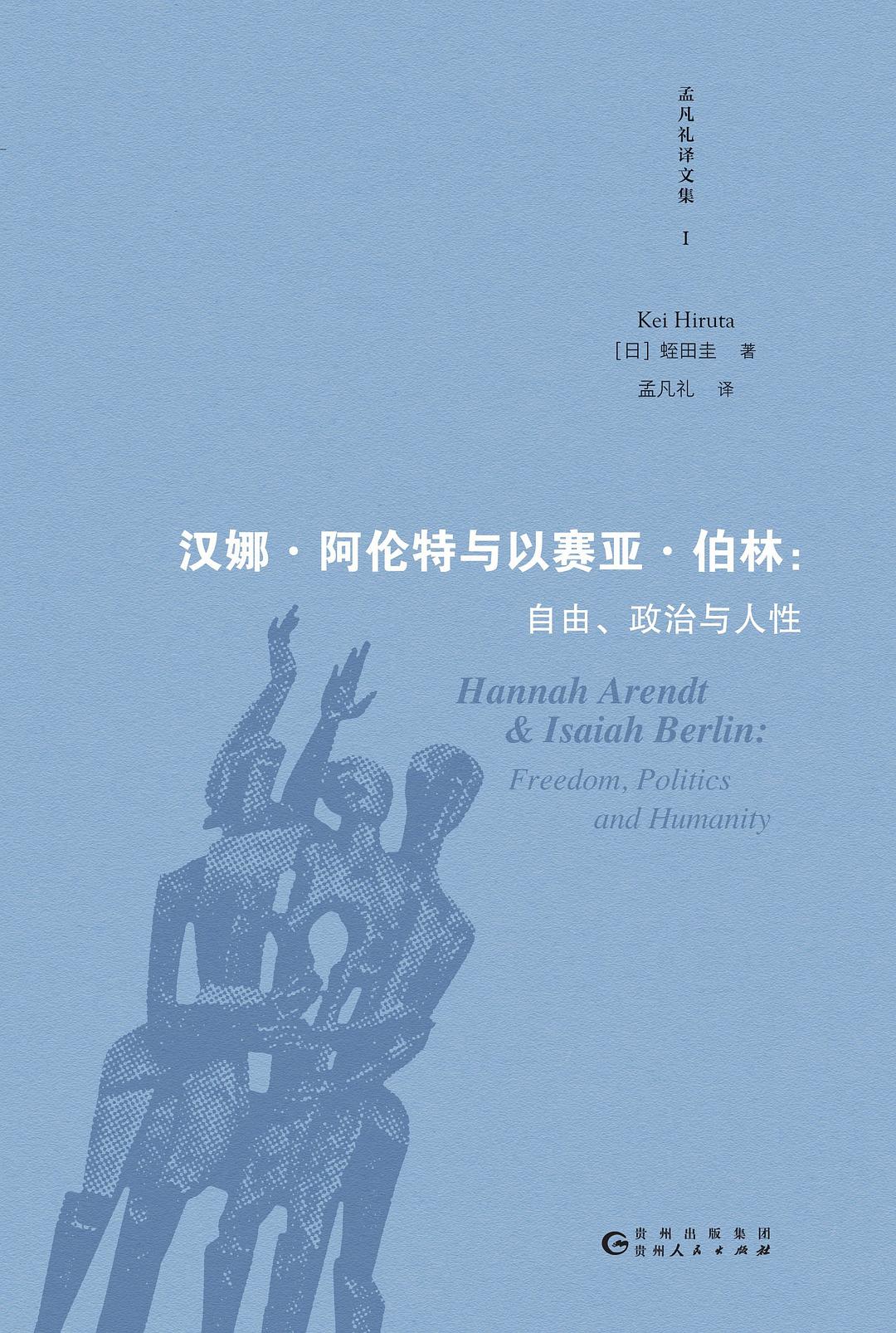
《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自由、政治与人性》,[日] 蛭田圭著,孟凡礼译,贵州人民出版社丨汉唐阳光,2024年9月版,480页,98.00元
日本青年学者蛭田圭(Kei Hiruta)的《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自由、政治与人性》(Hannah Arendt and Isaiah Berlin : Freedom, Politics and Humanity,2018)以二十世纪这两位最重要的思想家之间的思想分歧和冲突关系为研究焦点,运用了思想史和政治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且利用了大量新的档案材料,首次全面而深刻地追溯和还原了两位杰出思想家的相遇、冲突、分歧的过程,在此基础上阐释了他们之间在政治、哲学、历史等核心问题上的根本性分歧,以及这些分歧如何为研究二十世纪的政治理论和哲学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
在中译本出版之前,旅日学者王前教授撰写了长文介绍这部著作,为读者阅读该书提供了相当详细和富有启发性的导读,文章最后说“经历过至暗时刻的他们留下的思想对我们思考当今的政治和社会依然极有参照意义”(王前评《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我就是讨厌她”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2-05-17,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056696)。说得很对,这也正是中译本出版后马上受到关注和好评的原因。
蛭田圭在“引论”中指出:“压迫、统治、非人性和政治的颠倒,既是他们的生活主题,也是他们的思想主题;自由、人性和政治也是如此。”(第7页)从“生活主题”到“思想主题”,“压迫、统治、非人性和政治的颠倒”是对他们所成长的那个纳粹时代最准确的概括,也是当代政治学、历史学和伦理学等研究论域仍然必须关注的核心议题。还应该说的是,该书无论在文献解读或观念阐释方面都显示出作者具有扎实的研究功力、敏锐的问题意识、力求客观与公允的评论立场以及清晰的表述能力,这也是它受到好评的原因。
书名中的副标题“自由、政治与人性”无疑就是关于阿伦特与伯林的思想分歧的主题词:在第二章论述了两人的生平和敌意关系的发展过程之后,第三章讨论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们关于“自由”的理论分歧;第四章考察了较长时期中他们对“非人性”和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不同认识;第五章围绕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和伯林对它的评论展开论述;第六章探讨的是他们中后期著作中对于什么是理想政体的不同看法,在最后的“结论”中谈到了他们的思想分歧对于当今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的影响。作者认为,他们的理论分歧的核心,一是“人之为人意味着什么”;二是对极权主义的不同观点,以及由此引出的抵抗极权主义的可能性等问题上的分歧。综合起来,我认为真正的核心问题就是对极权主义的认识。从作者的立场和方法来说,他申明不是为了支持谁,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思想,包括把他们所隐藏的偏见也梳理出来并给予批评性的思辨。
从阿伦特与伯林的关系来讲,问题的确比较严重。为什么伯林对阿伦特非常不喜欢,说她代表了“我最厌恶的一切”,乃至对她有着“终生的仇恨”?有人甚至怀疑伯林对待阿伦特的态度是一种厌女症。而阿伦特对待伯林的敌意则是以冷漠和怀疑的态度进行回击,她的立场与性格在分歧中同样毫不容情。那么,他们之间的分歧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调和的吗?阿伦特和伯林的经历与思想渊源固然不同,但两人都是犹太移民知识分子,都是自由的捍卫者,都同样反对极权主义。应该强调的是,这种共同性非常重要。蛭田圭认为,“事实上,阿伦特和伯林有时被视为属于同一群体,这是有充分理由的。20 世纪 80 年代共产主义东方的持不同政见者看到了这两者的相似之处。为想象一个更好的未来,他们中的一些人既从阿伦特又从伯林的反极权主义著作中寻获灵感。”(261页)这是从一个比较独特的角度而言,其实更应该从两人的思想立场上看待这种共同性,蛭田圭在该书中就不断对这方面作出阐释。
对于我们而言,在他们的思想分歧之上的共同性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作者所讲的,“他们都是当代事件的直接见证人(目击者)……当一个事件在他们眼前展开的时候,他们有记录这个事件的特权。我们的两位主人公都见证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些决定性事件,有时写下了历史的第一份粗略草稿……”(331页)当然,即便同样是历史的见证人,所写下的文章还是会有观点上的不同,但是他们在根本的立场和态度上是相同的,与他们根本区别开来的是对待现实采取回避的立场和态度。蛭田圭在这一段论述中的焦点显得似乎有点模糊,但主要意思是对的:相比于“当时和现在世界上一些哲学教员所特有的虚伪和不真实”,“我们两位主人公的作品都具有直接性、紧迫性、诚实性和权威性”(332页),也就是具有直面现实、知行合一的品格。由此还引申出一个所谓的“学术性”问题,他们的学术著作都招致过“不够学术”的指责。有意思的是,蛭田圭说:“这项指控部分有效,但也可能被解读为一种赞美。而这正是更超然的学术所缺乏的。……回过头来看,我们两位主人公的生活和作品最打动我们的是,它们都体现了苏格拉底的格言:真正的哲学必须是活的。或者更确切地说,‘真正的哲学是根植于激情的知行合一。’”(同上)说得更精准和深刻的是这一段:“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主人公都决心直面他们时代最紧迫的挑战,并彻底思考这些挑战,不受知识分子的怯懦及其孪生兄弟‘学科约束’的阻碍。”(333页)与此相反的是回避现实、扭曲历史、为纳粹党人的权力崛起和征服野心大唱赞歌或“学术地”背书的学术大腕,他们显赫的声名总有一天会成为耻辱,这是未来的学术史研究肯定不会回避的研究议题。
蛭田圭正是在这样一个面向现实还是逃避现实以及关于思想品质的层面上揭示了他们共同性与差异性,以及阐释了对他们同样表示敬意的理由,这一大段话值得在此引述:“阿伦特富于她在理论著作中所称赞的一些美德,如勇气、对世界的关怀、反对舆论的不公正和对真理的热情。甚至她那些一直受到猛烈攻击的缺点,如不知变通、道德主义和苛求,也可以说是来自她的思想的积极品质。同样,伯林的个人品质,无论好还是坏,都与他的理论观点相一致。它们一方面包括正直、慷慨、成熟和谨慎,另一方面包括自满、优柔寡断、胆小和安于现状的偏见。人们可能对阿伦特的同情大于对伯林的同情,或者反过来也一样,这取决于一个人的气质和思想取向。但我们可能都同意,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意义上过着思想家的生活。由于这种‘言行一致’,我们的两位主人公都赢得了我们最高的赞誉和钦佩。他们不仅给我们留下了杰出的思想,也是我们的榜样,即使他们所代表的观点彼此不同。”(同上)就此而言,当然也会对阿伦特投以更大的敬意。
说到他们之间的不同,早在1941年的纽约就已经有所表现。虽然都力图反对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但是他们的参与方式和性格是不同的。伯林是政府雇员团队的一员,总是试图与英国的目标保持一致;阿伦特总是寻求成为独立的声音,为各种媒体撰稿,更关心说服民众。她说:“因为我认为没有什么比抗击纳粹更重要,所以我自然不会假装在忙别的事情。”(25页) 当然,该书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思考伯林和阿伦特在看待以色列问题上的分歧——更应该说是撕裂,这对于今天来说就很有现实意义。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二战期间的美国,阿伦特给伯林的印象是“她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狂热的犹太民族主义”,激烈的程度让他感到“太夸张了”(27页)。到1949年他们在哈佛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伯林又发现阿伦特彻底改变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变为一个“攻击以色列”的人(31页)。关于阿伦特的这种转变有多种解释,蛭田圭主要通过对她发表的文章《犹太复国主义再思考》(1944年)、《拯救犹太家园》(1948年)和《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九章《民族国家的衰落和人权的终结》(1951年)进行分析而得出自己的结论:她反对的是官方的犹太复国主义,“从阿伦特的角度来看,她从未背叛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复国主义背叛了它自己”(34页)。而伯林对她的转变不能理解是因为他并不知道阿伦特对犹太复国主义态度的全部复杂性和微妙性,因此把阿伦特的转变视作令人震惊的背叛(37页)。
真正使两人关系撕裂的是1961-1962年轰动世界的艾希曼审判。阿伦特去耶路撒冷旁听了公审,然后写了一系列文章,后来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f the Banality of Evil,1963;安尼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为书名结集出版。伯林也去耶路撒冷看见了被告和“半个小时左右”的审判,但他认为审判对于犹太人的国家会带来不利后果。而阿伦特则通过对审判的分析、研究提出了具有爆炸性争议的观点:犹太人的被屠杀是否只是纳粹的责任和罪行?用蛭田圭的话来说就是:“阿伦特挑战当时有罪的德国人和无辜的犹太人之间的明确区别,尖锐地批评了她所认为的犹太领导人在处理纳粹问题上的失败。”(63页)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第七章,阿伦特指控当时犹太人组织的领袖出于各种原因、以各种方式与纳粹合作;她认为事实上如果没有犹太人的组织和领袖,即便会有混乱和大量的痛苦,但受害者的总数不会多达四百五十万到六百万。这一指控马上引起爆炸式的反响,人们纷纷指责她是为纳粹开脱罪责,对犹太受难者缺乏同情。
另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是关于“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准确的翻译应为“恶的平庸性”,在此暂从多年来中译本已流行的习惯译法),批评者认为她的这一说法降低了艾希曼罪行的严重性。对此蛭田圭的解释和看法是比较清晰的:“事后来看,她的基本观点并不像批评者认为的那样有争议。她的主要意思是,一个人不需要成为一个非常邪恶的人来犯下非常邪恶的罪行;相反,一个没有深刻动机的平庸之辈(比如阿伦特眼中的艾希曼)可能在骇人听闻的罪行中扮演重要角色,只要他或她没有思考自己行为的真正意义。……不过,阿伦特当时的读者却有着不同的反应,他们真的不能理解她所说的‘平庸’是什么意思。虽然她的捍卫者喜欢指责读者没有努力理解她所要传达的意思,但我认为她对造成混乱负有部分责任。尽管她决定在书的副标题中使用‘平庸的恶’,但却没有阐明这个挑衅性短语的意思:这个短语在书中只出现过一次,但作者却没有提供定义;……”(66页)这样的分析是比较公允的,阿伦特的表述的确有不严谨或不充分的地方。
关于阿伦特提出的“平庸的恶”所蕴含的意思,德国学者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认为:“阿伦特是想通过她刚刚形成的这个概念提醒人们注意这个现象,即恶很可能是一种不起眼的常规性的组成部分。一个干出大屠杀这种惊世骇俗的恶行的人,在正常的社会环境当中也许就是个‘小丑’一类的人。……他或许是个循规蹈矩的职员,也许还是个和蔼可亲的父亲。”(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和思的故事》,陈春文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405页)这一解读更贴近对人性的分析,也更是人们在各种磨难经历中不断观察到和体会到的事实。阿伦特认为纳粹暴政的罪恶应该分为最高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与下面的执行者或被统治者中的参与者的“平庸之恶”。所谓“平庸”是指作恶者本身并非真正的恶魔,而是平庸的也有可能是平凡而恪守职责的公务员,其基本的人格特征是无思想、无真正判断的能力和勇气、只会盲目服从;在此基础上呈现的“恶”是指面对显而易见的恶行不但不加限制,而且直接参与到恶行之中,没有良心不安或道德上的自我谴责,在日后的审判中还以只是执行命令、职责等借口为自己开脱。尽管对于阿伦特以这个术语表述对艾希曼审判的看法存在很多争议,但是它在一个基本问题上是确凿无疑的:在像纳粹那样的邪恶政治体制中,目睹体制的邪恶行为而保持沉默、服从体制的安排而参与到邪恶的行为中去,这些都是不容抵赖的邪恶,不能以“国家行为”或“执行命令”的借口得到赦免。这是阿伦特在纳粹帝国与体制下每一个人的行动选择之间搭建起来的道德审判,也是在阅读纳粹帝国历史的时候最具有个体性的维度之一。
关于“平庸的恶”的起源与个体性,还应该联系到汉娜·阿伦特写于1928年的博士论文《爱与圣奥古斯丁》(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J.V.斯考特、J.C.斯塔克编,王寅丽、池伟添译,漓江出版社,2019年),因为她在六十年代重新修订这篇博士论文的同时,正在经历对纳粹主义尤其是艾希曼现象做深入研究并投身论争之中。在“平庸的恶”这个概念中所隐含的对物质、权力、虚荣心和道德顺从主义的焦虑,已经出现在对被奥古斯丁所诅咒的“城”的分析之中,使她很自然地把原来就已经认识到的奥古斯丁思想中的贪欲观念、死亡观念和存在主义思想往极权政治的邪恶方向思考。具体到对于艾希曼“平庸的恶”的来源的分析,“她所看到的艾希曼,是陷入到奥古斯丁所描述的受死亡驱迫的地上之城(civitas terrena)中的居民。他完全被自身的平庸以及这种平庸对他野心造成威胁的恐惧所消耗;他的中下阶层出身、低教育水平和早期的寂寂无名,对他来说无异于一种世俗的死亡。为了摆脱这种因害怕永远不能获得他个人渴望的一切而产生的恐惧,艾希曼在纳粹等级制里寻求不断的称赞和奖赏。因此,他也可以毫不犹豫地将成千上万的人送至真实的死亡。在这过程中,他还为‘小人物’发明了一种‘康德式’的道德以迎合那些有权力支配他的人的期望,这种道德将德国中产阶级的社会价值和元首的授权意识形态融为一体。在坚称那个在耶路撒冷的胆小怯懦而又雄心勃勃的低能儿是真正的艾希曼(即使其核心空无一物)这一点上,阿伦特是对的。”(J.V.斯考特、J.C.斯塔克,中文版序言,第4页)那些为了摆脱自身的平庸与寂寂无名而积极卖身投靠纳粹体制、忠实执行罪恶职责的人,既是可恶的也是无耻的。
接下来更重要的问题是,格鲁嫩贝格认为在阿伦特的报道中实际上还隐含着一个她一直在追问的问题:“人们到底应该怎样对待极权统治下的责任消失问题?如果责任的载体突变为极权统治下的不知不觉的受命者,人们又该怎样重建责任伦理?”(同上)这的确是非常重要、必须追问的问题。在格鲁嫩贝格看来,阿伦特并不认为执行命令和集体参与的犯罪就不是犯罪、行为者就不用负责,在任何条件和情况下都不能开脱所犯罪行的责任。
那么,现在可以回到蛭田圭在第五章“邪恶与审判”中对于因艾希曼审判而引起分歧和争议的分析。在澄清了针对阿伦特关于艾希曼个人及犹太人领袖的评论的常见误解之后,蛭田圭着重研究了伯林对阿伦特1963年的这本书的道德反对意见。在此之前他已经说过,伯林在这个问题上关于道德冲突与道德困境的思考比包括阿伦特在内的同时代大多数哲学家都要深刻(206页)。伯林力图强调的是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尤其是犹太人领袖所面临的那种极端情境中的道德困境,由此表明别人无权在事后指责他们的选择,更不应把纳粹的罪责也分摊一点到他们头上。蛭田圭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析相当细致、深刻,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阿伦特和伯林同意,如果一个人的选择自由被彻底否定,他不能受到指责。但是对于这种‘选择自由的彻底否定’是只发生在集中营内部,还是也发生在集中营外部,他们则是分歧的。”(239页)这个问题在这一章的结论中有更准确和深刻的表述:“从思想层面来看,在艾希曼争论中出现的两位思想家之间具体的道德分歧,是与其他分歧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包括对极权主义压迫和支配性质的历史分歧,以及对高度压迫条件下的自由及其限度的理论分歧。”(261页)
在这里还必须谈到蛭田圭在前面第四章的“结论”中谈到的他们两人关于极权主义的不同认识和理论:“一个侧重于社会、经济和制度因素,以追踪极权主义的起源;另一个则侧重于观念因素,梳理极权压迫的内在逻辑。一个认为集中营是极权主义的核心;另一个认为乌托邦主义、科学主义、家长主义、一元论和积极自由是极权主义心理的组成要素。”(198页)过去我曾经更倾向于认同伯林的极权主义心理要素理论,但是后来发现阿伦特以纳粹集中营为极权主义核心的视角更有穿透力,只要不把“集中营”的概念固化在奥斯维辛这样的实体之中,它所代表的暴力与恐惧就是阿伦特所指向的极权主义的最核心定义。
关于政治与自由的问题,蛭田圭认为这是他们所有分歧中最根本的一个,概括起来就是:阿伦特认为政治存在的理由就是自由,只有在政治行动和言论中人才能恰当地回应作为人的条件并充分实现其潜力,得以确认在世界中的存在;伯林则认为消极自由是更真实、更人性的理想,因为人是一种做出选择的动物而不可能是其他。他们都认为自由对人至关重要,隐藏在他们对自由的争论之下的是对人的条件本身的更深层次的观点分歧,也就是说“生而为人意味着什么”(131-132页)。
德国政治家艾尔哈特·艾普勒(Erhard Eppler)认为阿伦特关于政治的理想论述如果作为理解政治的学术性导论是不恰当的,但是用作政治的纠正却很重要,比如阿伦特关于“政治的意义在自由”、哪里有命令和服从哪里就没有了政治等等这样的观点,它传达的信息是“政治与自由有关”(艾尔哈特·艾普勒《重返政治》,孙善豪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33页)。这位偏向左翼的社民党政治家极力强调政治与自由的价值联系,这也正是阿伦特的政治与自由论述的核心:政治的意义和承诺是自由。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关心在今天政治与自由的关系与意义的问题?在阿伦特看来是因为极权主义和原子弹所带来的经验点燃当前时代政治的意义问题。此二者为这个年代的根本经验,如果无视这些经验,就会像从来不曾活在这个世界一般(汉娜·阿伦特《政治的承诺》,蔡佩君译,左岸文化出版,2010年,143页)。对政治与自由的经验在她看来就如同对生活经验一样重要,是一个人是否“活在这个世界”的重要判定标准。我们的经验当然也是这样:在我们的所有关于社会公共事物的深入讨论中,在所有对于任何个体生存经验的追问中,政治意义的问题和自由的问题必然出现。那么,重返关于政治与自由的对话,就是要重返“活在这个世界”的真实经验,就是要重新获得真实的自我与真实的生命。
蛭田圭在全书的结尾部分指出,阿伦特和伯林无疑都有各自的缺点和优点,即使他们的作品都曾被歪曲、偏见和轻率的判断所玷染,但是它们没有许多当下新康德主义者的毛病——对历史的盲视,无法为具体行动提供指导,不愿意解决他们“学科范围”之外的问题,并倾向于将未经检验的假设和文化偏见带入所谓的理想化理论(335页)。这又回到了前面所讲的那个面向现实还是逃避现实的问题。假如在这个层面上评价阿伦特与伯林与今天现实世界的关系,那么西蒙·斯威夫特(Simon Swift)关于“为什么是阿伦特?”的回答是特别有分量的:“汉娜·阿伦特是我们急需的批判思想家。在她晚期有关美国政治和文化的许多文章中,阿伦特论及了许多在今天仍与我们相关的问题,比如公民自由的性质、国家支持的暴力问题,以及自‘越战’以来政治中的谎言和犯罪文化。”(西蒙·斯威夫特《导读阿伦特》,陈高华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年,11页)他在全书的最后继续回应这个问题:“我们当前的政治危机乃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新黑暗时代,全球各地的赤裸生命正以各种日益令人不安又陌生诧异的公开方式遭到残酷对待,面对这些现象,阿伦特仍是我们不可或缺的思想人物。她的这种对新政治的呼唤,从未像今天这般迫切。”(同上,176页)说得很对,在这种语境中伯林恐怕难以走在阿伦特的前面。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