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期的官员王守仁(1472~1529年)——他更为人所知的笔名是王阳明——在讨论摇摇欲坠的明朝的军事需求时,转而求助于《孙子》与《吴子》这些中国最受尊崇的军事著作。而他在谈论良知与圣人时,则转向了《孟子》。王阳明作为一位深有造诣的军事家,他知道孟子反对暴力和战争;鄙视梁惠王“好战”;曾斥责齐宣王,怀疑齐宣王“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发现梁襄王的欠缺,劝他说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在16世纪,没有人把孟子奉为战争方面的权威;虽然他给统治者提供了如何向民众灌输军事勇气的建议,但这方面的思想完全被忽视了。

王守仁
无论作者是王阳明—(一个监督过几次军事行动的文职官员),还是大将军戚继光—(一位写诗并与各类文人混在一起的军官),军事问题都只能依照古代兵家传统来加以讨论。这种文学传统(最好的例证就是《孙子兵法》)可能是在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当时的职业竞争日益两极分化,政治谋士强调仪式和美德,军事谋士则强调秘密和欺骗;在王阳明和戚继光的时代,兵家著作长期以来一直是高度竞争的考试体系所用的课本。
就像那些国家支持的其他正统学说,如朱熹(1130~1200年)对儒家思想的诠释一样,成千上万的学生年复一年地学习《武经七书》,希望通过考试获得晋升;那些学习朱熹的人想要当文官,其他人则要参加武举考试。这两种知识传统有相似的发展轨迹,经常互相借鉴,同时又正式地否定、抵制或忽视对方。要想在任何一个领域取得成功,就必须同时精通这两个领域。理想中的将军深谙哲学,最受赞誉的文官则经常组织民兵来镇压土匪团伙。而且,这些考试在许多方面都有重叠——人员、结构、地点、程序,等等。那些熟谙兵书和骑射技能,且身强体壮,因而有资格参加武举考试的人,有时具有与通过文举考试的人相同的文学技能。
许多文人观察家嘲笑清朝武举考试的文学内容,但那些爬上这一成功阶梯的人所留下的散文、诗歌和学术著述,证明了他们对文学文化广泛而深刻的熟识。让我们来看看1734年刊行的《山西通志》上的一首诗《途次逢寒食》。
何处来春风,
淡荡开晴旭。
不见杏花红,
才逢柳梢绿。
这首抒情诗是马见伯在太原总兵任上所作。和他的表兄、兄弟以及他们的曾祖父一样,马见伯也是武举考试的佼佼者。尽管传记记载马见伯通过了陕西乡试、在北京举行的会试和康熙皇帝(1654~1722年,1661~1722年在位)主持的殿试,但现存的武举文献都没有提到他。1691年秋,他通过了会试和殿试,被授予武进士。
1703年,马见伯任太原总兵官,这是一个武进士常任的职位;太原作为山西省省城,战略位置重要,在1672年到1731年被置于两个武状元和另外三个武进士的管辖之下。在这段时间里,只有另外九个人担任过这个职位,其中两个人的资格与武进士相当:一个是内务府包衣,另一个则是御前侍卫。在五年并最终延长到十二年的任职时间里,马见伯向康熙皇帝呈递了一份奏折,在奏折中,他揭露了非法猎枪的广泛存在,并提出了没收它们以及控制火药生产的建议;这些建议被及时地接受了。两年后,马见伯上呈了一份更为雄心勃勃的奏折。
《武经七书》,注解互异,请选定一部颁行。又祭先师孔子时,文臣自驿丞以上官员,皆得陪祭。武臣惟副将以上,方准陪祭。请将武臣亦照文臣一体行礼。
这是根据《清实录》所记述的奏折内容,但其他文献能告诉我们更多的内容。虽然《清史稿》在大多数细节上(或者缺乏细节,我们之后将会看到)与《清实录》一致,但它确实承认,马见伯要求儒臣来选择正统的军事经典,并明确地将奏折与前一年所宣布的一项法令联系起来:康熙皇帝对那些参加武举考试的人的素质表示不满,并敦促那些在智力和体格上合格的绿营军人把考试作为晋升的手段。然而,《清史列传》和《国朝耆献类征》(这两部书中的相关段落内容大体相同)讲述了不同的故事。
根据这些文献,马见伯提出了三个而不是两个请求。除了《清实录》中记载的建议之外,据说他还建议奖励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军人:那些通过武举乡试并且能解释孔子的《论语》的人,应该被授予职位。

康熙皇帝
1710年11月10日,康熙重新审查了这些之前被兵部否决的提议,他的反应非常积极。长期以来,对武举考试的持续不满,促使他发起并批准了一系列改革,但他从未想过要改变课程设置。相反,他在箭术考试中考虑了距离的问题,把通过殿试的很多人都分配给了禁卫军,并鼓励汉军旗人参加考试,同时还有其他的一些变化。《清实录》记载了康熙皇帝对马见伯的提议不同寻常的个人且深刻的回应:
《武经七书》,朕俱阅过,其书甚杂,未必皆合于正。所言火攻水战,皆是虚文。若依其言行之,断无胜理。且有符咒占验风云等说,适足启小人邪心。昔平三逆、取台湾、平定蒙古,朕料理军务甚多,亦曾亲身征讨,深知用兵之道。《七书》之言,岂可全用。孟子云,仁者无敌。又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日若欲另纂一书,而此时又非修武书之时。……孟子有言,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若知此意而用兵,方是。总之仁者无敌,此是王道。与其用权谋诈伪无稽之言,不若行王道,则不战而敌兵自败矣。王道二字,即是极妙兵法。从古穷兵黩武,皆非美事。善战者,皆时至事迫不得已,而后用兵也。昔吴三桂反时,江南徽州所属,叛去一县。将军额楚往征之。有人献策于贼云,满洲兵不能步战,若令人诱至稻田中,即可胜之矣。岂知满洲兵强勇争先,未及稻田,已将诱者尽杀之。此献策之人,亦为我兵所杀。用《武经七书》之人,皆是此类,今于《武经七书》内,作何分别出题,及《论语》《孟子》,一并出题之处,著九卿定议具奏。
皇帝只在此处表达了对正统武举考试课程的极度蔑视。在其他任何地方,他都没有提倡将《孟子》作为将领的参考书。皇帝酷爱火器,热爱优秀的弓箭手,看重勇敢的猎手和有成就的将军,但军事理论对他来说是如此陌生,以至于当他想起那些将保护他的宫殿以及成为绿营军精锐军官的人时,他选择赐下一部谴责“好战”之人的文学作品。
没有一位中国哲学家明确表达过自己的反战立场。对军事冒险最直言不讳的批评家墨子(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坚持认为,惩罚性的战争往往是必要的。这与孟子在各种对话中所持的立场相近。正如历史学家李训祥所指出的,这也接近孙膑(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和其他兵家的立场。虽然孟子毫不犹豫地直面不守诺言的统治者——他曾强烈谴责梁惠王——但文本的编者在《孟子》结尾部分,对好战分子进行了最严厉的抨击,这大大削弱了“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之类话语的影响力。有时候,孟子的言论听起来像是在为战争辩护,但康熙皇帝在说出了军事开脱的通用方法,最后以“迫不得已,而后用兵”结束时,违背了孟子哲学的精神和文字。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他重复了“王道”一词。
在与梁惠王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交流中,孟子描述了统治者对臣民的责任:“王道”一词只出现在这里,而没有在其他地方出现。孟子在解释需要一套规章制度来保障民生时,巧妙地在其论点中加入了一些关于暴力和战争的类比——这样的类比既能与其对话者的好战冲动产生共鸣,也能揭露好战冲动与不那么明显的好杀政策之间的联系。在谈到有大网眼的网与合适的树木砍伐季节时,孟子提倡一种以社会稳定为前提的保护之道,这是任何一个勇武君王都无法保证的。臣民愿意为保卫由好君王统治的土地而战,但他们不应该被要求为了开疆拓土抛家舍业。孟子对战争的态度显示出一定的矛盾,他甚至似乎相信统治者可以合理地对自己的臣民使用军事力量,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言论与他的核心信念一致,即统治者必须为其臣民的最大利益行事。
以马见伯的奏折为基础,康熙皇帝关于准备武举考试时使用儒学两大主要文本的谕旨出现在《清实录》的最后:自次年开始执行,直到乾隆皇帝取消这一改革,每位参加武举乡试和会试(仅次于进士的两级)的考生都要写一篇约六百字的文章,对《孟子》或《论语》中的简短篇章做出回应。尽管参与文举考试的人从未被问及兵书,但他们通常会被问及如何处理军事问题;他们被要求对镇压土匪等问题有实际的把握,同时对军事史有学术上的了解——比如,1851年徐河清在科举会试中所写的策论就是一篇探究军队阵法的文章。
在后来的几年里,康熙皇帝采取了更大胆的措施来改革武举考试制度。他似乎觉得自己培养儒家将领的实验是成功的:四年之后,他打破了文举和武举考试制度之间的传统障碍。在乡试和会试中,通过资格考试的考生可以从一种途径转换到另一种途径。有些人甚至这样做了。
让我们退一步,在1710年的这场戏剧中插入一个停顿。当康熙皇帝认真思考马见伯奏折提出的问题,思考如何提高武举考生的受教育水平时,他最信任的官员李光地(1642~1718年)插了一句:“令习武者读《左传》即佳。”皇帝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但我们会仔细考虑。
多年来,李光地的日常任务就是审阅被授予武进士之人的试卷。在1688年、1706年、1709年和1712年,他担任武举殿试的读卷官,而在1691年,他担任武举会试的知贡举,但从他的序和奏折来看,他对这些考试不怎么感兴趣。他对文举考试的评价则截然不同,他强烈谴责那些官员的不道德和不明智,他们通过贿赂玷污了自己的高位,让无耻的考生获得文进士头衔;而这鼓励了来自福建的那些野心勃勃的历史学家,他们围绕在李光地的身边,以其道德正直,确立起一种崇拜。
虽然李光地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儒家思想的贡献,但他在制定军事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主导平定了台湾,甚至还涉猎了军事理论——他的《〈握奇经〉注》完成于1700年。陈其芳指出,李光地主张哲学融合和哲学真理的实际应用,并将他看成韩德林(Joanna Handlin)在《晚明思想中的行动》(Action in Late Ming Thought)一书中提到的吕坤及其他学者的追随者。
虽然李光地在1710年武举考试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寥寥几笔就可带过,但他与马见伯职业生涯的交集表明,他可能影响了马见伯对于考试课程的思考,反之亦然。我想,在十九年以前,李光地作为武举会试主考官,一定知道马见伯的名字,因为在那一年,马见伯通过了会试和殿试,获得了武进士头衔。
当然,这两个人是在大约七年后认识的,那时他们的事业使他们再度相遇。下面是李光地对弟子所讲的故事,后者将其记录在李光地的年谱当中:
公督学时,过正定与[马见伯]语,器之,至是,拔以自助。公尝阅河出,夜宿舟,次更既阑,披衣启舱,见一人左韔弓矢,右跨刀,闭息坐舱门外,呵之,则见伯也,诘其故,则谨对曰:“公野泊于外,警守不可以懈,防遏意表,中军分也。”公笑曰:“际时清平,复何所怵?而君达晓凝座,无乃惫乎!”见伯曰:“凡为将者,日夕警惕,倘床簟偷安,习久益惯,何以备疆场驱策乎!”公深为嘉叹,后累荐之。
在这件回顾性的逸事中,对马见伯的描述表明,他在清军中担任一名忠诚而明智的军官时,并没有摆出一副博学的样子。他严肃地提醒他的文官上司,皇帝所坚持的军事价值观——这位皇帝坚持要文举考试的满人考生在射箭和骑马方面表现出才能。但马见伯1710年的奏折表明他有高超的策略手腕。这份奏折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包括在孔庙祭拜的内容,这可能不会让审阅奏折的高级文官高兴,但皇帝作为奏折的接收者,于二十年前在孔庙观礼的时候,就已经呼吁军事官员与文官一起参与——马见伯的建议可能是刺激皇帝进一步改革欲望的开胃美食。这份奏折提出的第二个建议并没有完全让皇帝满意;但李光地本人尽管在帝师的职位上工作了多年,却没有预见到弟子的思想会发生怎样的转变:《左传》取代或补充军事经典的建议立刻被否决了。
尽管皇帝根据自己的战争经验形成了介绍书籍的理由,并坚持认为他对几次战役的指挥使他懂得了从《孟子》获得军事建议的重要性,但他还是欣然接受了李光地的观点。李光地的一篇奇怪文章出现在他去世后编订的作品集《榕村语录》中,在这篇简短的文章中,有两点与正在讨论的事件产生了共鸣。第一点,长期以来孟子被认为是一个完全脱离军事问题的思想家,但对战争,特别是战略问题,他有最深刻的理解;第二点,《孙子兵法》中所表达的思想无法被接受。在第一点中,李光地引用了皇帝提到的一句话,即“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在第二点中,李光地特别挑出“火攻”来批评,就像皇帝所做的那样。他还直言:“若将《左传》《国策》《史》《汉》诸书,选集一部兵法,当胜于今所谓《七书》者。”最后,他提到了马见伯。
据我所知,李光地这篇身后文章没有确切的时间。马见伯死于1720年末,李光地则在皇帝批准马见伯提议的八年后,先于他两年去世。人们想知道的是,这篇文章在皇帝做出决定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马见伯给其保护者的提议所采取的形式,在更多的证据积累起来之前,都只能是假设。
清代每次乡试、会试和殿试的结果,无论是文举还是武举,都会在贡院内(或者紫禁城内的殿试处)被高度程式化的文字记录下来。其中一种记载类型是《题名录》,只概述具体考试的内容,记载参加考试之人和通过考试之人的姓名和职务。另一种内容更为丰富的记载是《试录》,其中包括前言和附言,主考官在附言中提供了考试的许多细节、对军事和民事问题的思考以及一些成功考生所写的范文。在许多情况下,清代的武举考试记录构成了兵学传统学者的唯一书面遗产,他们继续为国家服务,在民政与军务、帝王与平民、满人和汉人的重要交汇点担任要职。
五十年来,从《孟子》和《论语》中抽取的作文题目是武举考生面临的第一个文学考试。最初,考试里出现了其中最明显的段落。在课程改革后举行的第一次武举乡试中,福建和云南的考官都出了关于《论语》当中著名一段的题目,孔子在这段话中列出了政府应该提供的东西——“足食,足兵,民信之矣”(12.7)。在其他地方,考官让那些新冒出来的考生讨论“仁者必有勇”。康熙皇帝的改革也影响了其他问题,即出自三部官方兵书(《孙子》《吴子》《司马法》)的问题,以及自1064年以来一直是武举考试标准要素的实际政策问题:与传统不同的是,前者侧重于那些与儒家思想产生共鸣的章节,因为它们涉及礼仪、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军人文学素质的重要性;而后者则包括《孟子》和《论语》中的章节,并请考生对最近的课程改革发表评论。
尽管没有文献提到武举考试考官之间的交流,但一项关于从《孟子》和《论语》中摘录的用于考试的段落的研究表明,存在这种横向交流的趋势。例如,1711年福建和云南使用了《论语》的同一段落;1726年,山东和顺天也使用了《论语》中的同一段落;1741年,湖广湖北(当时的一个行政区域)和江西也使用了《孟子》中的相同段落。在从兵书经典中摘录问题方面,这一现象也很常见:在同一年的考试中,两三位主考官使用了《孙子》《吴子》《司马法》的相同段落。在同一时期,其他省份出了其他题目,这似乎表明没有从政治中心发出的综合命令来决定考试题目。与此同时,在康熙皇帝于1710年颁布改革科举法令不久后,武举考官和考生都对康熙皇帝的统治予以明显的关注。因此,1711年顺天武举考试的主考官吴廷桢和1711年四川武举考试中以《论语》为主题之范文的作者韩良卿,都强调了“王道”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在一段时间内,官方语言都带有帝王苛责的印记。
报考文举的考生需要对朱熹所注释的儒家经典中的段落进行评论,而往往相当浅显且基础的文章就能让武举考官满意。因此,彭楚才在评论《论语》中“事君能致其身”一段时,简单地对比了统治者和父母关于个人身体的主张,认为每个人的身体暂时属于统治者,但在去世后被归还给其父母。然而,也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一些武举考生的学习已经变得跟文举考生类似了。
为了认可朱熹的解释优势,例如,韩良卿在1711年四川武举乡试中使用了与这位宋代思想家相同的提法“帝王之道”来解读经典。同样,施礼在对《论语》中“其养民也惠”一段做出解读时,使用了与朱熹一样的方法,描绘了发问者(子产)的政治背景,并引用《左传》中的一段话作为其论述的一部分。如果李光地看到这部古代编年体史书经常被武举考生引用,他可能会感到很满意:除了考题所依据的五本标准经典之外,在考生中最受欢迎的题目被康熙皇帝以不合适为由加以拒绝。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1月4日,经由兵部议覆,正考官戈涛(1751年进士)起草的两份奏议得到了皇帝的批准。乾隆已经不是第一次拒绝其祖父对武举考试制度的激进改革了。
在描述了于武举考试笔试部分(内场)使用铃声并提出了预防措施之后,戈涛接着谈到了另一个问题。“武乡会试 ……自当以武经为重。四书[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旨义,非武士所能领会。”在呈上这份奏折的时候,戈涛已两次担任乡试考官:1754年江西文举乡试的辅考官和1757年云南乡试的正考官。然而,虽然许多考官在某一年举行的文举考试和武举考试中连续任职,戈涛却并不是这样,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相关武举考试的记录当中。尽管如此,这位缺乏经验的官员的观点似乎与皇帝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取消关于《论语》和《孟子》的考试题目,将使事情有所好转。戈涛在奏折最后甚至进一步指出:“亦应如所奏,择文理粗通者,即予中式,以示矜全。”
自从康熙皇帝表示要有一种不同类型的武进士以来,已经过去了近五十年,但时代的发展决定了不同的需要。乾隆皇帝开展了积极进取的军事行动,将疆域版图拓展到西藏、新疆和蒙古草原,并对八旗军队以及特别是绿营军提出了要求。康熙皇帝将军事文化理解为儒家文化的一个分支,想让时间之河倒流,使帝王谋士文武兼修,乾隆皇帝则接受了孔子、孟子、墨子、孙子等人对“文”与“武”之领域的区分。
从十一个月之后举行的乡试开始,谋求高级武举功名的考生将被要求讨论《孙子》《吴子》《司马法》中的段落,但他们再也不必讨论王道、霸道或者孝道了。
在本章的开头,我提到了王阳明的著作,他是一位文官,严格区分武事和文事。但有一次,王阳明确实将《孟子》纳入了关于军事问题的讨论:在仕宦生涯早期,他曾试图改革武举考试。王阳明认为边疆地区是脆弱不安的,国家有责任建立一支在技能上不局限于骑射的部队:如果不了解战略,军队就无能为力。所以在1499年,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制度,那是一种与考试挂钩的训练计划,强调军事理论和决策,学生要从精英家庭以及明朝的军事院校中选拔。他坚持训练必须尽快开始。毕竟,孟子自己就曾说“苟为不畜,终身不得”。
这不是李光地和其君主的言语或推论,而是这位年轻官员精心提交的奏折中对孟子作为军事圣人的明确诉求。在后来的奏折中,他再也没有说过这种真心话。五百年后,那些在回避使用暴力的国际限制的情况下大谈道德征伐的人,也把他们的计划与拥有无可置疑的道德凭据的学说联系起来。康熙皇帝朝这个方向的努力,即为中国两位最伟大的哲学家赋予伟大军事意义的尝试,注定无法成功。
(本文选摘自《古代中国的军事文化》[美]狄宇宙(Nicola Di Cosmo)主编,袁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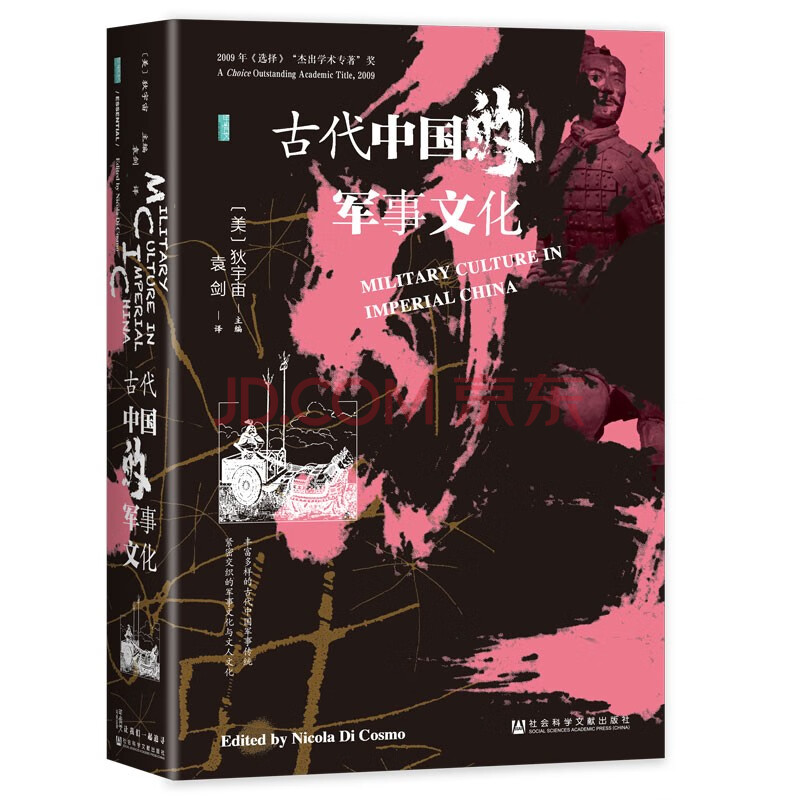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