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热的8月,刚结束在成都蒲江明月村的驻留项目,返回英国没几天,颜歌便赶到爱丁堡国际图书节,和瑞典作家安杰伊·蒂奇(Andrzej Tichý)一同分享创作短篇小说的感受。一年前,颜歌的短篇小说集《在别处》(Elsewhere)由英国老牌出版社费伯出版社出版。这部短篇小说集是颜歌首次用英文写作的文学实验。作为同样在异国他乡生活,对“身份认同”感到疑惑的亚裔女性,我被颜歌的坦诚、清晰和果断吸引。

颜歌在爱丁堡国际图书节。颜歌198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2015年开始定居爱尔兰都柏林
写短篇小说像是进行快速约会
颜歌年少成名,代表作包括《关河》《良辰》《异兽志》和“平乐镇三部曲”《五月女王》《我们家》《平乐镇伤心故事集》等,她的近作、长篇小说《平乐县志》于2023年10月在中国出版。
分享会上的颜歌一如往日般大方得体,还带着点儿幽默。“这是我用英文写的第一本书。我之前一直用中文写作,主要写长篇小说。我尝试用英文写作,在某种程度上,这似乎可以缓解我作为一名中文作家的中年危机。回想起来,这有点天真。当时的我并不想安于现状,想进行不同的尝试。我用英语写作,写不同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不仅内容不同,风格也不同。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像是在进行快速约会(speed dating)。在摆脱了某种长期关系后,我也想试试这个。但我很快意识到,我的想法有多么天真,因为我发现,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有着本质的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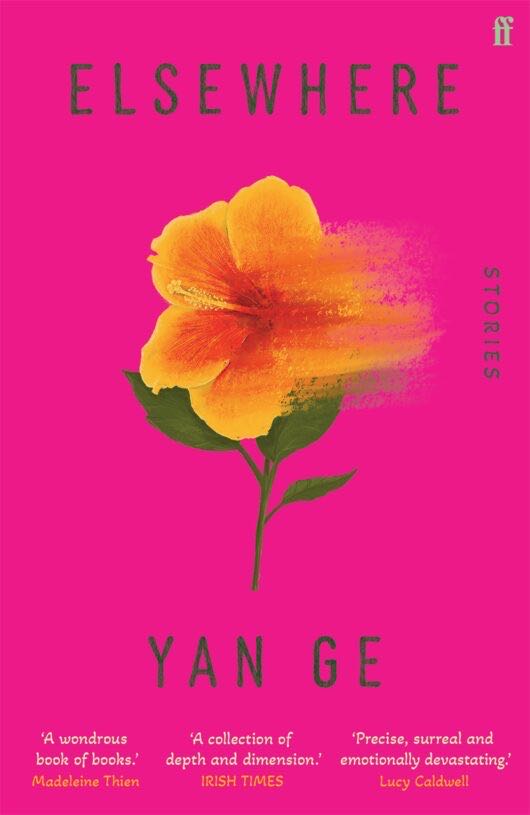
去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在别处》以英文写作
《在别处》中包括九篇短篇小说,这九个或诙谐或奇妙的故事,发生地从中国到爱尔兰都柏林,从伦敦到斯德哥尔摩,既有当代的,也有古老的,既有真实的,也有超现实的。和写长篇小说相比,颜歌表示写短篇小说并非是一件舒服的事情,甚至要困难得多。“我觉得短篇小说其实更接近诗歌,而不是长篇小说。如果我必须对它进行总结的话——当然进行总结本身是有点反文学的。但从根本上来说,一部长篇小说,无论是对于作者还是对于读者,都会让对方沉浸进去。面对一部长篇,刚开始,你总会有点手忙脚乱,但是,到了中期,你就会发现,小说像是到达了某个点,在这个点上,它就会顺从你,然后,你就会稳定下来。而短篇小说呢,我认为它们总是在挑衅着你,会令人无法安顿。它永远不会给你那种感觉,比如,满足感。”
颜歌目前在用英文创作长篇小说《目的地酒店》(Hotel Destination),这部作品的英国、北美版权已经售出。显然,长篇小说似乎更能让颜歌游刃有余,即使是英文的。颜歌在分享会上表示,“对我来说,短篇小说创作是一种不同肌肉群的锻炼。”她继续解释,“我不觉得我可以自豪地称自己是一名短篇小说家,我只能算得上是一名短篇小说爱好者。我读了很多短篇小说,我试着写一些。但我觉得我的写作方式,从根本上来说,还是长篇小说式的,这一点在我的短篇小说集《在别处》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就是书里面的短篇其实都是比较长的短篇。我感觉我没有写真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
颜歌坦言自己写的短篇小说可能有点“差劲儿”,但她是短篇小说的“死忠党”,并用“great”来形容写这种类型的小说的心情。她说:“从很多方面来说,写好短篇小说要难得多,因为它总在挑战你,你总得改写,你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它从头到尾都具有抵抗性的,它从不屈服。并且,你必须在写作中与这种不安感斗争,要以某种方式驾驭它,又要保持那种不安感。我觉得这是一次有趣的旅程。”
用英文写作,感到“孤独”
颜歌一度很排斥英语写作,认为她的文学创作的语言只能是中文。她曾表示,在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英语无孔不入,而用中文写作,是她抵御英语入侵的最后堡垒。她甚至说:“我永远不会用英语作为我的文学语言。”不过,2016年,颜歌开始用英文写作,作品发表于《爱尔兰时报》和《刺人虻》等媒体。她在分享会上解释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改变。
“从根本上说,因为我被英语逼得走投无路了。我在英语环境中生活,所有的事情都用英语……有一天我在都柏林,我试着写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都柏林,是在英语环境中发生的,我意识到,我必须用英语写这个故事,因为用中文写的话,很多地方需要翻译,而我的翻译能力很差。从那时起,我有了更多只能用英语才能写出来的故事。我不得不成为一名英语作家。这个身份和用中文写作的身份有所重叠,因为两者都是作家,但两者又有许多不同。最开始,用英语写作令我感到兴奋、奇妙,特别是在创造性方面对我提出了挑战,让我这个正在写作上经历中年危机的作家焕发出新的活力。”
“这很有趣,也很痛苦,因为你不得不在这门新语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最让我感到恐惧的是,我无法看清我的读者。当你用母语写作时,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你生来就使用这种语言,你用这种语言写作,你的写作对象是你的国人,他们与你有着相同的语言、相同的文化和文学背景等,所以你们就像是在同一个池子里,可以相互交流。而当你用不同的语言写作时,你就离开了这个池子,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你表面上是在用别人都能理解的语言进行创作、交流,但语境已经完全改变。当每个人开始作为写作者写作时,她或多或少是在面向读者写作,这些读者不一定是某个真实的人,但他们非常重要。而我在英语写作中没有这种感觉。当我和我的经纪人一起整理这本短篇作品集时,我想,谁会读这本书?我们是否应该在故事结尾附上一张十英镑的纸币……这样人们就会觉得会有收获?”
虽然有很多困惑,但面对刚启航不久的英文写作之路,最好的答案也许就是坚持做自己。颜歌很释然地表示:“在某种程度上,这对我来说也许是一种来自上天的馈赠,比如,这种‘孤独’的感觉。我想这也是我离开中文写作时想要的:我想‘独自一人’。这就是我现在的处境,虽然这并不怎么令我感到愉快。”
写作是自然而然地发生
当安杰伊·蒂奇提到从边缘写作时,颜歌认为两人都是从他们所处的环境进行写作。她表示:“这一切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我认为,什么可以写进文学作品,什么是怪诞的,什么是优美的,这一切都与特定语言、文化和文学传统所认定的中心有很大关系。我在写作时做出的选择或多或少都是在浑然不知中做出的:我想保持这种方式。无论已经写了多久,我都希望一切都能够自然而然地发生,这有点像是直觉。
“我觉得我们在这里谈到的很多东西,都和文化偏见有关。《在别处》的开篇故事叫《小房子》, 其中有一个情节故意迎合人们的刻板印象,即认为中国人爱吃奇怪的东西。我拿这一点使劲做文章,以一种非常夸张的恶作剧的方式,让阅读的人感到难受……在想象的世界里,在想象的读者面前,我认为感到难受就是让他们开始自我审问的一部分:你从哪里开始难受的?你站在这个地方,我猜这是你的世界的中心,你是否愿意换一个角度去看、去理解、去试着感同身受,而不仅仅是厌恶和心烦意乱?总之,在某种程度上,我呈现那些怪诞的图像是为了挑战读者,让他们思考,这到底是一种生理反应,还是一种文化偏见。”
“我认为这也是文学的作用。我想到了我最喜欢的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的一个著名的观点,他认为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具有政治性,因为政治将动物的喊叫与人类的声音区分开来……我认为文学也是如此。文学改变了我们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以前被认为是边缘的东西,并思考为什么会有边缘。比如,我们如何认定历史、政治、经济的中心?我们又如何将其颠覆?或者我们如何建立一个新的中心?我经常思考这些问题,因为我是一个福柯主义者。我经常思考这些问题,但同时,我也尽量不去在写作的时候思考这些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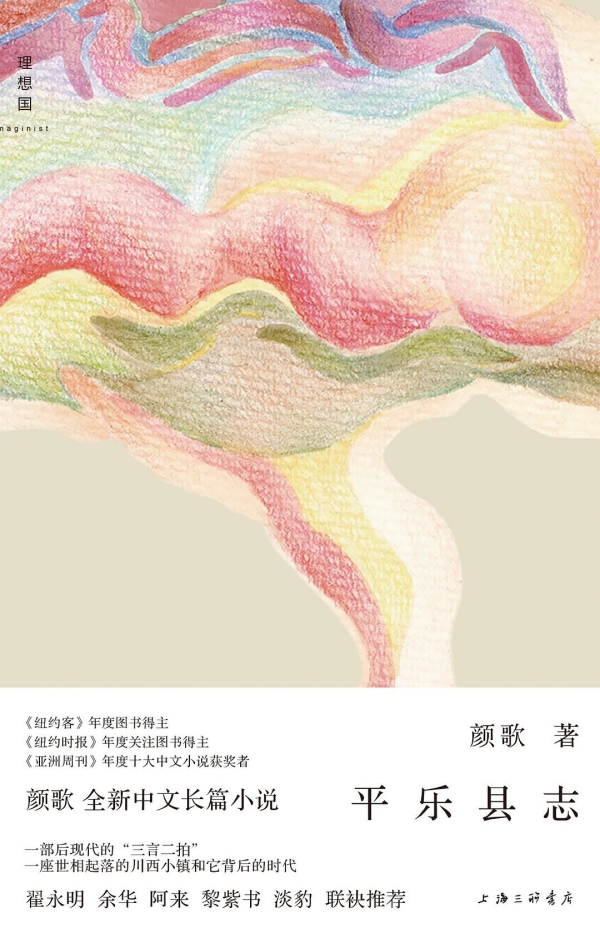
颜歌去年出版了中文长篇小说《平乐县志》
“我永远是一个局外人”
在分享会的提问部分,有观众提问颜歌:所生活的不同国家、文化是如何影响她的世界观的?颜歌回答,她的经历自然而然地成为她的认知的核心,她需要跳出自己的躯壳,去认真审视,才能理解这一点。
她说:“近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到中国。然后,我自然而然地感到非常内疚,因为这就像是,我放弃了我的精神故乡。我开始焦虑,开始内疚,我试着想出某种理论来安抚自己。”
颜歌从“身份认同”这里获得了一些疗愈。她解释:“当我们谈论身份时,它不应该是单一的,它应该永远是多重的。因为我们都有多重身份,比如,我是一个母亲,我是一名作家,我也是我自己。也就是说,你具有各种各样的身份,即使你只用母语写作,只在你的祖国生活。当你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切换时,这种变化就更会发生。所以,如果说我从我的经历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我已经逐渐接受了这种永远的焦虑和内疚。身份就只是一种吗?它真的是多重的,必须是多重的,并且,它也是变化的。我们无法真正确定什么,我们不能下结论,‘哦,那么颜歌,一个来自中国的作家,现在怎么样……’因为我们都在不断地改变,我们的观点在不断地改变,我们在不断地与世界和我们周围的人进行互动。这就是有趣之处。从根本上说,我认为文学的存在,或者说我们的写作,就是为了抵制把这种把事情固定下来的冲动。”
“我们拒绝被束缚,这就是我们写小说的原因。如果非要说它是如何影响我的世界观的,也许就是这样。我觉得我的世界观就是: 没有世界观。我一直都想变得更有好奇心,也许这更像是我从一个康德式的人转变成了黑格尔式的人。我总是喜欢展望未来,试图理解现在,并走向未来,而不是回望过去,去寻找什么绝对真理。当我踏上我的旅程时,我想,寻找绝对真理的想法已经离我而去。我想,我永远是一个局外人。”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