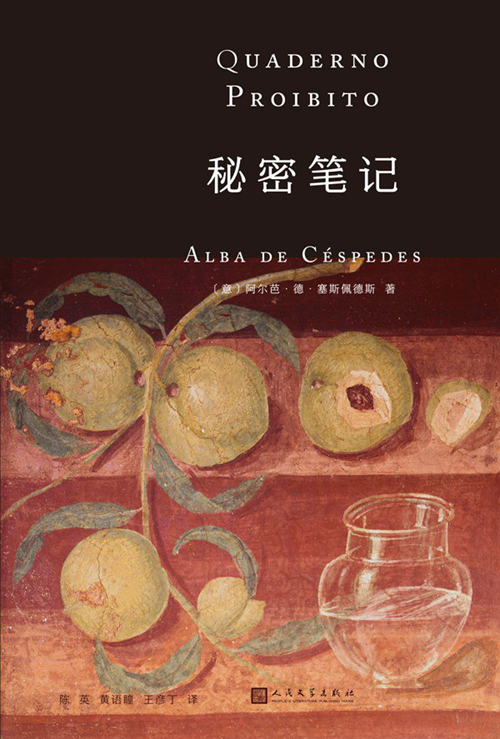
“在什么地方我可以更坦诚?”瓦莱里娅问自己。大家真诚坦率地围坐在桌边,但瓦莱里娅知道,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不在隐瞒,“我们因羞耻或恶意隐藏了自己。”意大利作家阿尔芭·德·塞斯佩德斯的代表作《秘密笔记》以日记形式纪录了她六个月的生活。给丈夫买烟时,她顺手买下了这个黑色笔记本,她写道,每天忙忙碌碌,一天结束时却好像什么事也没做。家里太小了,笔记本无处可藏,她甚至没有一个自己的抽屉。她为丈夫和孩子找机会出门,为自己找借口熬夜,好偷偷写日记,让身体里的河流涌动起来。如果发生的事没有被写下来,那个在日常缝隙间挣扎着现形的自己,就没有机会真正诞生。如果她永不诞生,没有人会记得它存在过。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黑色笔记本,但每个女人都必须销毁它,瓦莱里娅也不例外,这是让生活恢复光洁冰冷的捷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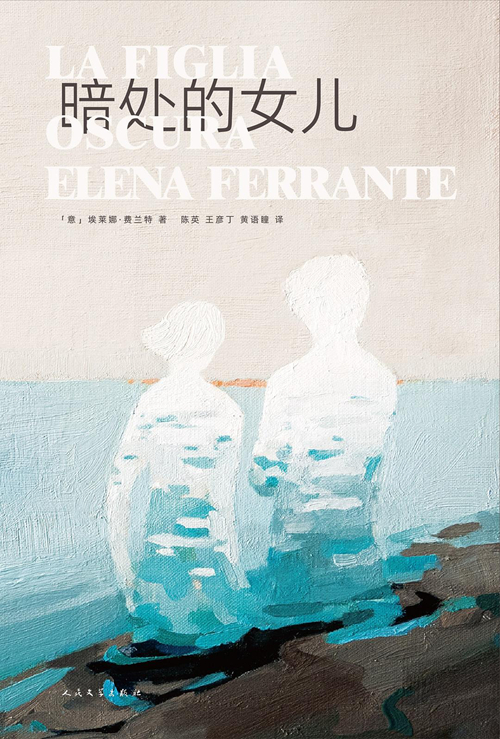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想过甜蜜的生活,但如果它只是掩盖无序的表象,总有人因为更渴望找回秩序而打破它。勒达正在享受的度假因为她腰部有了一个伤口而中止。她不能告诉任何人,这是一个叫尼娜的女人用她送的帽针刺的,因为她拿走了尼娜女儿埃莱娜心爱的娃娃,并眼看着埃莱娜因此病得厉害,把尼娜的生活变得一团糟。她不能这么说,因为大家会问她为什么要拿走那个娃娃,她认为自己也不知道。当然她知道,这是埃莱娜·费兰特的第三部小说《暗处的女儿》,它是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复杂性精神”的直接体现,试着告诉我们事情总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女儿去往多伦多与前夫一起生活后,勒达决定去海边度假。早在前夫搬走之前,她就觉得是自己一个人创造了女儿,看到自己遗传给她们的女性特质。现在,卸下母职的勒达感到“很自由,却没有享受自由的愧疚感”。在海边,她遇到了一个喧闹的那不勒斯大家庭,和她的原生家庭一样,勒达很努力才逃出了那些说话总像命令的男人和沉默易怒的女人。只有年轻的尼娜像“躲过了某种规则”显得与众不同,也许是因为她心无旁骛当母亲的样子。勒达几乎每天在沙滩见到她和女儿埃莱娜,以及埃莱娜形影不离的娃娃,这对母女都像娃娃有生命一般对待它,又丑又旧的娃娃因此散发一种活力。勒达曾把自己小时候的娃娃送给大女儿比安卡,那些年勒达很沮丧,她把自己逼到了“母亲”与“自我”只能择一的绝境,当感觉到一个欺负娃娃的三岁孩子比自己强大,她动用了镇压的权力,狠狠推了比安卡一把,抢过娃娃。又发现娃娃全身被记号笔画得很脏,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但当时我觉得已经没法挽回了,那些年里,所有一切在我眼里都无法挽回。”她把这个“肮脏的东西”扔了出去,和比安卡一起看着来往的车辗过了它。
勒达眼里的孩子带着对自己的盘剥和敌意,对此她已经很克制,却还是使用了暴力。她用沾着比安卡眼泪的手继续打她,或对她大喊大叫,就不能自己好好待一会,妈妈从来没有自己的时间!在五岁的比安卡想学妈妈把果皮削成蛇的形状却割伤手边流泪边流血的时候。比安卡又一次向勒达提出将果皮削成蛇形状的要求,是在勒达离开两个月后回家。“她们越是盯着我,我越强烈感受到她们之外的精彩生活。”满怀期待的孩子不仅不能让勒达和家庭空间和解,反而推她逃离,她不能看见孩子的需求比自己的更强烈。削完橙子她就又走了。三年。

《暗处的女儿》电影海报
费兰特对待自己的小说人物,就像这些人物对待别人一样残酷。她让勒达注意尼娜和埃莱娜的一举一动,来意识到她们母女拥有的亲密对她而言多么陌生。她让尼娜成为下一代勒达,是她对女儿失去的耐性让生活变糟。她让勒达将娃娃视为母女情感的纽带,而埃莱娜只是借丢了娃娃缠住她害怕失去的妈妈。直到小说结尾尼娜刺伤勒达之前,只有勒达藏起的那个脏脏的娃娃,像磁铁勾起勒达很久没有想起的事,一次次用嘴里吐出的污水或虫子,尖锐的展示回忆对她的报复。三年后勒达同样出于利己回归了家庭。哪怕只是回想起这份快乐耗尽,和取而代之的残忍感觉,就连她和成年的女儿分开后的轻松都被推翻了。此时,勒达拒绝做尼娜的同谋,不仅如此,还选择这个时机向尼娜坦白,是自己拿走了埃莱娜的娃娃。
母亲们需要勒达,由她代替自己释放内心膨胀的黑暗能量,母亲们需要一场如此逼真的恶梦,只要她们找准时机醒来。文学从根本上讲是危险的,波拉尼奥说,对作者而言更是如此。“要能够接受你所发现的那个事实,即便有时候它沉重地压在我们身上,比覆盖在所有已逝作家的遗骨上的石板还要沉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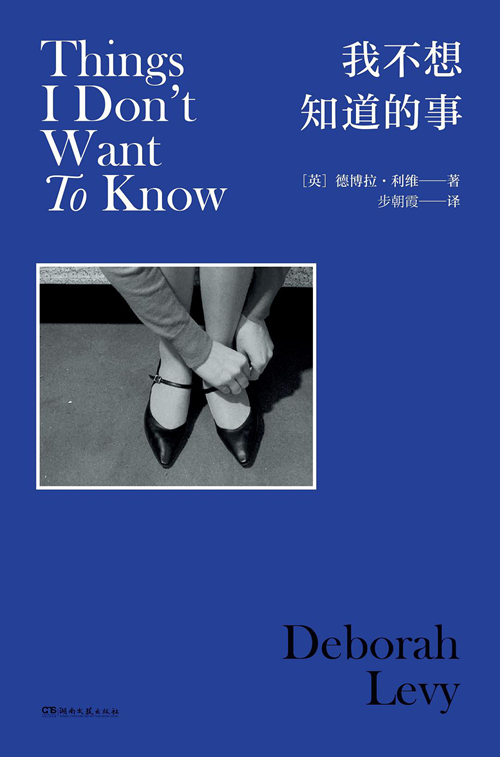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写作?英国作家德博拉·利维列出以下四个理由:政治方面的目的;历史方面的冲动;纯粹的自我中心;审美方面的热情。它们构成了女性成长三部曲的第一部《我不想知道的事:论女性写作》。这其实是一本洋溢着黑色幽默的生活纪录,首尾两部分记录了当下,二三两章则分别回顾了她在南非度过的儿童时期和举家移民英国的青少年时代。宏大的标题被利维演绎至她人生的细枝末节,存在的范畴突然改变了它们的意义。
德博拉·利维那年春天过得十分艰难。她把自己送去了玛尔帕岛,到旅馆附近已是半夜,她在黑暗中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感叹在生活中无路可走时,实打实的迷路不禁让人释然。也许这可以解释,德博拉的笔锋为何也总是落在“实打实”上。行文中她的视线似乎是有形的,打开行李收拾时,总会带着的转换接头和一根延长线;把浴室海报的“骨骼系统”错看成“社会系统”;来找她的旅馆主人玛丽亚比上次见面老了不少,好像也更不开心了。越无关紧要的,越触发她的念头。巧的是利维也带着笔记本,她更愿意称之为法官札记,“因为我一直都在为自己不甚明了的事情收集证据。”当相似细节不止一次出现,证据就渐渐有了雏形。只要写下来,目之所及的,最终都会揭示真相。
打开法官札记,是几十年前她在波兰搜集的素材,其中包括戏剧导演索非娅·卡林斯卡给演员的建议,这些建议一直影响着她在写作上的探索:
说出想说的话,是指你觉得自己有资格说出内心的愿望。我们心怀期盼的时候总会犹豫不决,我的戏剧想表现这份犹豫,而不是隐藏起来。犹豫不是停顿,是要把愿望压回去。但如果你愿意正视这个愿望并把它说出来,那么即便你的声音很小,观众也一定能听到。
父亲不是剧作家,但他的狱中来信同样建议利维,想法要大声说出来,不要只在脑袋里想想。她却决定把它们写下来,当她写出自己的思绪,“几乎是我不想知道的一切。”德博拉五岁时,南非奇迹般的下雪了,父亲和她堆了雪人,那天晚上,她正计划着明天要给雪人披一条围巾,父亲被警察带走了。利维在一所修女学校里,第一次学会了“言外之意”,讲述自己的过去时,她成功把个体历史还原成一个孩子眼中的样子,充满推理的谬误,却十分接近真相。父亲被带走时,保姆(也叫)玛丽亚抚摸她的头发,边哭边对她说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就可能进监狱。“玛丽亚”是个“方便白人叫”的名字,为了谋生,玛丽亚把自己的孩子送回家,让别人的孩子窃取她的精力,每一天结束时,她都坐在走廊啜饮一罐炼乳。这一幕,是利维离开南非时,唯一想保留的有关的记忆。到了英国,她逃去餐厅练习写作,但很难开口说给她上的菜没有煮熟,因为她是在流亡,而不是在生活。
利维也没有说明如今遭遇了什么,只描述一种结果,搭乘自动扶梯时,止不住的眼泪经常找上她。她来到玛丽亚为人们建立的、逃离家庭的避难所,思考着“母亲”是带政治色彩的一种妄想,揭穿这个妄想让我们内疚,也让我们担心为孩子建造的这个神龛会坍塌,于是试着压抑自己,“结果发现自己在这方面颇有天赋”。她认为在女人的说法上,没有人比杜拉斯说得“更残酷或更仁慈了”:她们在日复一日的绝望中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合法领地。那么,玛丽亚呢?玛丽亚严肃悲伤地离开了这个一手创造的地方,她已经努力过着剔除妻子和母亲日常职责的生活,是什么让她非走不可?“是隐藏在政治语言背后的谎言,是关于我们性格和人生意义的种种谬论。”这是同为“二十一世纪的出逃者”的利维得出的结论。
利维讲述的是犹豫这个故事本身,是人的一种困境,人们在找出路之前,先要想明白自己是怎么一步步走到这儿的。当利维在伦敦的自动扶梯上哭泣的时候,非洲就找上了她。自认为已走出的困境仍与自己藕断丝连,比如旅馆离桌子最近的插孔在洗手池上方,是供电动剃须刀用的。因此,利维最需要的,是那个转换接头和那条延长线。

必须和母亲一起生活,这是比利时导演香特尔·阿克曼的困境。她被卷入母亲正在死去的生活,反覆为无法承受的结果做准备。这一切没有把她变得仁慈,她为自己感到残忍、愚蠢、羞耻,母亲想要亲亲她,她躲开了,母亲要她说说话,她找不到有什么值得被提起。等待手术的一个月里,母亲说她闷得慌,如果手术后还活着,日子还是闷得慌,阿克曼这样想,倒没有说出口。不过她写下来了,《我妈笑了》是她陪伴母亲最后一段时光里写下的自传,向母亲之外的其他所有人散播坦白的力量。
阿克曼很早就明白,受教育越好的人越虚伪,啊,虚伪这个词也是学校教的,阿克曼发誓以后不会再用了。当学校老师向母亲提到你女儿头脑有些不一样,她认为母亲想到的只是一头秀发。不是垂死让母亲和她彼此无法忍受,垂死也没有更紧密地把她们联系在一起。从小母亲与她之间过于紧密的关系已经导致了她情绪的疾病,紧密得她没有发现自己还有父亲,病得她厌倦了所有关于幸存者的故事。
母亲周身氤氲的焦虑感和多愁善感和她的躲避形成恶性循环。她把写作当成自己和母亲之间的屏障,不是真正的解放,她写的仍然是母亲。母亲同时成为了阿克曼想躲开的人和不自觉细致观察的对象。其中最无法回避的就是她的笑。起初是快乐的、也许是由衷的笑,当笑逐渐变成一种对并不好笑的事情作出的反应时,“我妈笑了”也伤感起来。读到她写母亲只有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想死,已近乎体验写作的暴力。母亲先经历了一次心脏手术,又摔断了肩膀,短期内又经历了一次手术。母亲总在等待着什么,但肯定不是死。
垂死的母亲和她一起参加婚礼,化了妆让母亲看起来更糟了,母亲对阿克曼的回应是,你也应该化妆。在一次昏迷中,她对阿克曼说你从前对我很凶,还有一次揭穿阿克曼“你在躲着我”。这些母親不再掩饰不满的瞬间,才能让阿克曼喘了口气。她说了事实,没有说我爱你。阿克曼很高兴,相信从此双方都会变得不一样。一个女儿需要实话,不是礼貌。尤其是一个擅于分辨“被说出但没被交谈的词”的女儿,和一个“睡梦中大声说出自以为没说出来的话”的母亲。阿克曼是唯一真实的人,可惜却因此难以被接受,除了实话实说,阿克曼只剩下“我不知道”。数一数这本书里“不知道”出现的次数,爱存在吗?我不知道。拍电影时像别人说的那样全身心投入吗?我不知道。这些“不知道”模棱两可,但都更偏向否认。另一些,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不知道发生过的事是否会再次发生,不知道从前的事是否真的已经过去了——则使她失去了真正的生活。
为了逃离被卷入母亲的生活,她想回到自己的生活,这是一个“非凡时刻”。阿克曼提出一个“非凡时刻”,当我们隐约感觉到某个真相存在时,一些事情会秘密地、缓慢地发生,有时慢得我们几乎忘了,直到真相出现,这个突如其来的非凡时刻会带来轻松和平静。她发现自己不拥有真正的生活。问题是什么是“真正的”,阿克曼觉得妹妹有真正的生活,但当我们看别人的生活,是否就像看一本书或一部电影,尤其容易察觉到不言明的真相。最后,她在“我们这代人”里找到了,这一代人是真实的,是她的归属,“我第一次对自己说,我属于这一代人。这是有意义的”。
会不会有人告诉瓦莱里娅,我们这代人不用再一心祈求生活光洁了,尽管这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利维把这种感觉形容为鞋里有三颗小石子,不知为什么,她并不想把石子取出来。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