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收获》2024年第4期以“青年作家小说专辑”为专题,刊登了《鹃漪》《吃黄昏》《夹竹桃有毒》《爆破游戏》《猎人之死》《拘鼠术》《七伤拳》和《工作狂博物馆》等八篇作品,引发了一定关注。由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上海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办,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王玮旭主持的“此刻·上海大学当代文学读书小组”,目前有14名中文系研究生、本科生成员,他们在近日就《收获》“青年作家小说专辑”进行了集中讨论,上海文艺将分三期呈现这些年轻的声音,本篇为第三期。
王玮旭:我们再来谈谈穆萨的《猎人之死》、倪晨翡的《七伤拳》和舒颖的《爆破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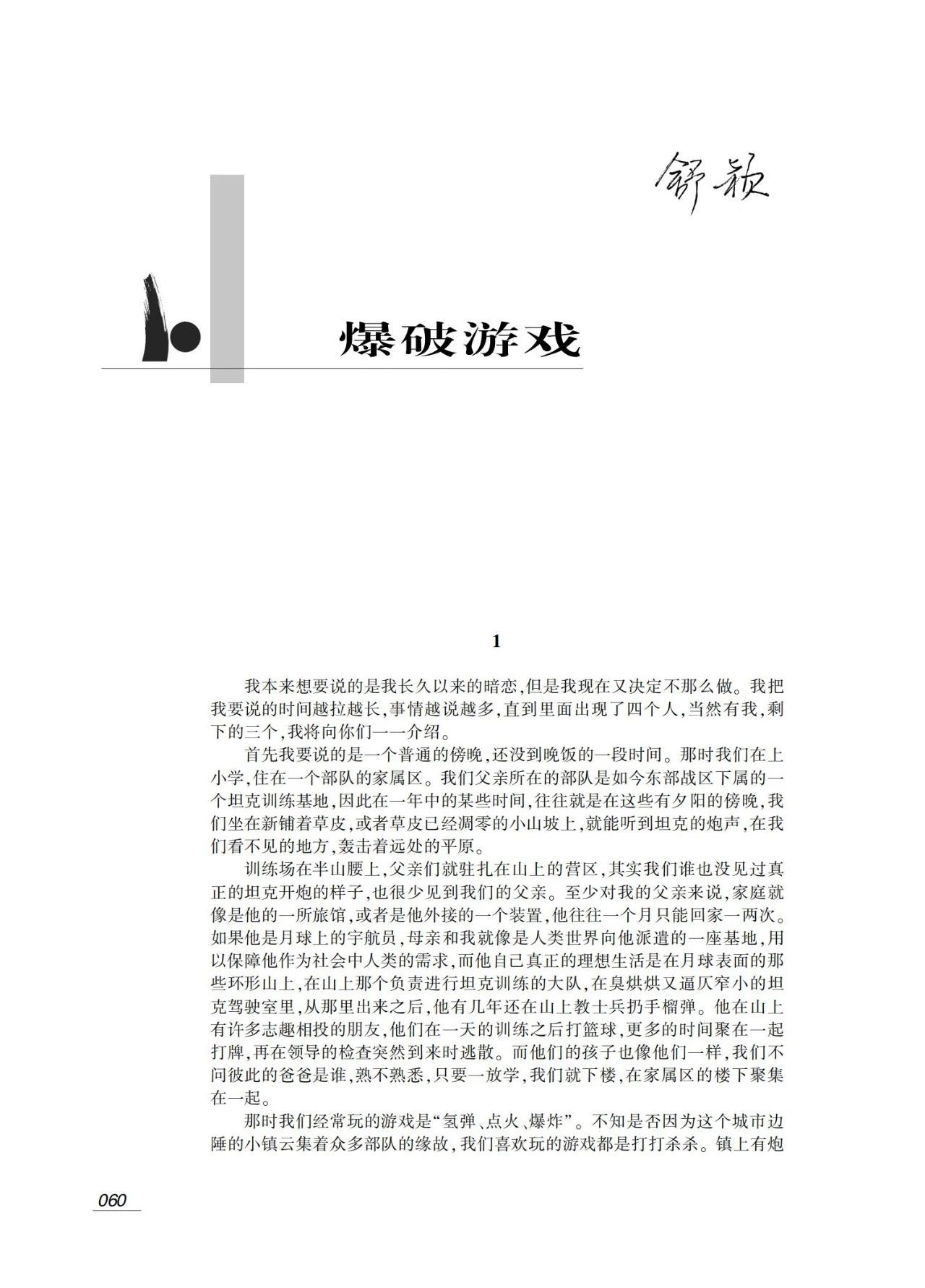
《收获》内页 舒颖《爆破游戏》
《爆破游戏》:弱点、深度与虚无
王佳颖:《爆破游戏》与《七伤拳》是一种作者与叙述者进行情绪对抗的写作:故事中的叙述者极度隐藏情绪使其不至于喷发,但作者却不断地追问。作者与叙述者形成对抗的力量,二者都在揭秘的一瞬间达到情绪高潮。
《爆破游戏》中,叙述者在隐藏并治愈一个童年的秘密。对于在部队家属区长大的孩子来说,部队的逻辑就是他们童年的逻辑,忠诚、勇敢、团结几乎是游戏的全部规则,而实际走向了这些规则的反面。我们以“勇气”诱惑黄琪茹走进山洞,又用“信任”一起结伴走回来以将功补过。这与现实中逃兵想要确认自己是否被发现其实并无异处,只不过军队的属性将这一人性的弱点放大了。我们与军人父亲们几乎没有联系,毛毛的父亲甚至是缺失的角色,所以只能用孩童视角去猜测军队属性是什么。于是当一个少年第一次尝试着用所谓“勇敢”怂恿另一个孩子走向危险,挣扎着体验什么是旁观他人的恐惧,在短暂到来不及品味快感的冒险后,陷入长达多年的如《罪与罚》般激烈的内心颤动。童年的记忆成为了旁观者的西西弗斯的石头而不是黄琪茹的。
张烨:《爆破游戏》的叙事者沉溺于记忆与叙事之间的不确定性、犹疑和跃动,小说中穿插的文学作品,以及“我”对时空迷幻的感觉,不断加深了这种虚幻感。小说常用的手法,是从现实的小事物写开去,最终总是变成某种抽象的东西。“我”的感觉只有在超脱出现实的时刻,才有可能(才值得)得以被“感觉”。小说的“我”其实非常切近当代年轻人的生活处境,难以将自己的感觉落在实处,总觉得现实生活不应该只是眼前的现实,而是有着某种更高、更深邃的存在,迷恋于制造“深度”,因为只有这种“深度”使得现实的生活能够忍受。换言之,“感觉爆炸”让创痛、平庸、难以忍受的日常变得值得活。
不过小说作者也许只是提供了这种体验,却难以为这种困境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我”决定探望怀孕的黄琪茹也许是一个办法,但小说的最后“我”还是无法逃脱这种生存方式:“我在心里说我还希望它能留得更深,让它永久地长在我的心上”。

舒颖
陈雨昕:童年玩伴、校园、恋爱等元素让《爆破游戏》在起初呈现充满感伤气息的青春文学面貌,然而当“我”逐渐鼓起勇重新带领读者回到那个恐怖的傍晚的那一刻,我们才真正察觉到积压在众人身上难以释怀的精神重负。
四人中,王子睿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他似乎受黄琪茹遇袭事件的影响最小,真正令其发生转变的是父亲工作上的巨变,现实的残酷被赤裸裸呈现在孩童的眼前,终使他以一种疏离又绝望的姿态面对世界;高中时期,加缪和黑塞的出场,更给其打上了荒诞世界中的孤独个体的印记,而他对《西西弗神话》的推崇也表明了他选择以何种姿态来应对荒诞和虚无的现代人基本处境。王子睿曾经用学科的差异来比喻对人生的看法,语文和数学都是拥有谜底的学科,前者是更为主观的意图,后者是接近绝对的真实,然而人类终不能揭开生活的谜底,因为生活本身没有尽头,也不存在答案,人被裹挟其中,无法超脱,在相同或是更低的位面上,人无法定义自己的行为,更无法得知生活的意义,这是王子睿的虚无。同西西弗一样,王子睿没有选择对抗虚无,而是接受虚无、承认虚无,以一种游戏的思维和姿态对待人生。“是游戏,就会有输赢,有时候你不得不去放弃一些,再去赢得另一些”,懂得取舍,接受输赢,这不仅是他做题的策略,也是他人生的法则。因为想要留住毛毛,放弃诚信,帮助她作弊;因为想继续利用父亲的人脉,放弃了奢侈的高考分数选择了其他省份的院校;因为信件被查,担心两边都受到波及,于是放弃了与毛毛的通信。在王子睿逐渐成长的过程中,他的冷静与野心慢慢显现,不出意外,终将成长为这个世界的优秀玩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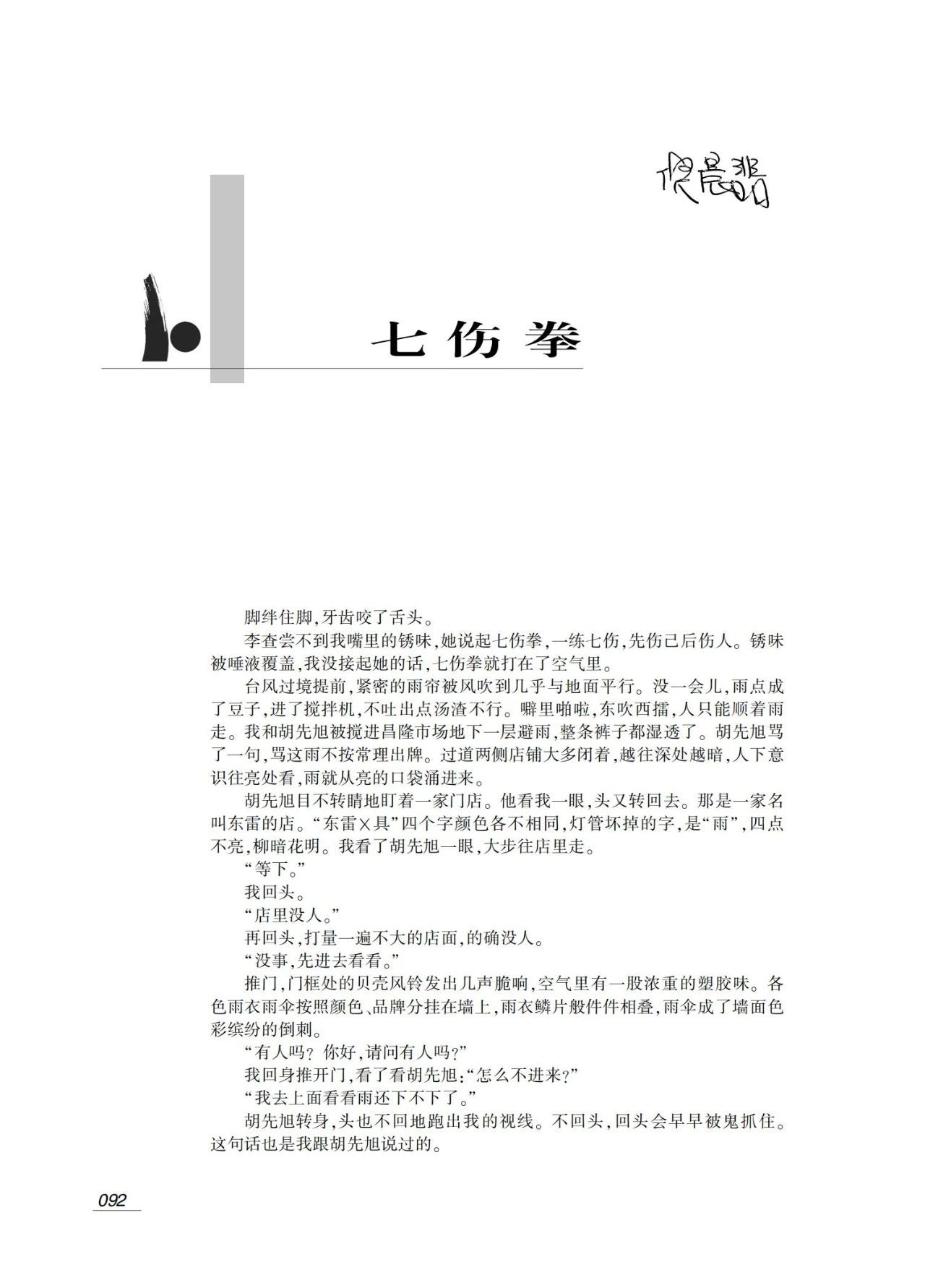
《收获》内页 倪晨翡《七伤拳》
《七伤拳》:困在关系网中的人
陈雨昕:《七伤拳》讲述的是由于家庭的重组给下一代造成的悲剧性结局。整篇小说给人一种悬置的不安感,生活的正常面貌在文中似乎看不到,字里行间中透露出的是强行接合的伦理关系的畸形与崩溃。而我们似乎也无法预测,这段脆弱的链接在“我”坦白自身的“罪行”之后,会发生新的、更加彻底的断裂还是从中生出新的纽带的触手?
张烨:我还是想回到“位置”的问题上,家庭中的三个人,都以一种近乎折磨自己的方式与别人相处:以好意掩藏着自己的真心,结果便是谁也没能真正地感受到幸福。对于母亲来说,对“我”的爱,多一分,容易变成怜悯,少一分,便是不公。于是,她只好用“捧一贬一”的方式表达对两个孩子的关心,将“我”设定为一个好孩子,她的“爱”才会顺理成章,实际上不过让“我”沦为了参照物,而“一旦衡量出了结果,参照物便失去了它的意义”。对“我”来说,爱是恒定的,所以需要掠夺,只有掠夺过来的,才不是怜悯的爱,而是因为自己值得被爱。可我又残忍地发现,无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得到母亲深层的、像对胡先旭一样无私的爱。母亲的“捧一贬一”,不过是为了隐藏起自己对胡先旭那无私的爱。对胡先旭来说,他活在异父异母的哥哥的阴影之下,自己本该享有的爱,被哥哥夺走,而母亲为了照顾哥哥的心情,不能肆意表达自己的爱意,只能以贬低自己的方式,掩藏起自己无微不至的关系。
小说中,他们坐在摩托车的一幕,最能表现出他们纠缠的关系,母亲驾驶着摩托车,胡先旭坐在前面,双脚不得不抵着摩托车的前车兜,屁股才不至于掉下去;“我”则在后面,双手死死扣着座椅的下摆,从不敢用手搂妈的腰。每个人都以别扭的方式掩藏自己的真心,因为摩托车已经摇摇欲坠,任何的变动都有可能导致侧翻。

倪晨翡
王佳颖:小说中,人物被解剖为关系网络的线索。在重组家庭里,我是我父亲的孩子,他是他母亲的孩子。故而当我失去父亲后,这个家不再平衡,每一个人都清楚彼此之间的关系如此微妙以至于每个人都有对感情强烈的渴求但每个人都小心谨慎。那些被怪罪在胡先旭身上的童年的错误是我这个无法在这个家中寻找到合适定位的孤儿的狂欢和收敛——并不为追求什么利益,但需要不断调整自己在这个家中的姿势以继续立足。而这小心谨慎也被作者层层拨开,作者在不断打乱叙述者的故作镇定,提示他每个人都需要活在一个被自己建立起来的参照系里。

《收获》内页 穆萨《猎人之死》
《猎人之死》:记忆的技艺
王佳颖:《猎人之死》中,比老皇猫的死因更为重要的是我要如何处理我的记忆。不同人对同一事的记忆往往有出入,对过去的真实的争辩即是不同记忆的争辩,人无法绕开记忆直接面对过去。作者试图给我们一些除了记忆的正确与否之外的可能性,例如有很多个平行世界,人有很多条命……此类对生命的其他可能性的允许并非有意的荒诞,而是提供一些关于如何与记忆和解的也许有效的答案:在前两个作品中叙述者紧张的“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隐瞒并不能成功,终被作者掘地三尺,反而是《猎人之死》中叙述者的轻盈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与过去的和解及自洽。
陈雨昕:在某种程度上,《猎人之死》和《爆破游戏》一样面临着存在之虚妄的难题。猎人老皇猫何时以及为何死亡的疑团贯穿全文,逼我们反问自身,所谓的真实性依靠的究竟是什么,记忆如何构成真实,我们如何想象真实。
“我”所面临的“真实危机”有两个,一是老猎人的死亡时间和死因,二是江媛对“我”的感情。人对于记忆之可靠性的认定不仅在于其符合自然或逻辑的通顺,尤为重要的还是构成该记忆的“毛茸茸”的细节。正是由于“两人”“野物”“啃”等零星字眼的存在,才与当下老皇猫在病痛中死去的鲜活事实产生强烈的矛盾冲突和张力,以至于“我”一直无法判定孰真孰假,以至于只能付之以平行时空理论。不过,相比起老皇猫的死,最终被定性为诈骗案的“我”与江媛的恋情则更具切身的荒诞感,当江媛一夜之间拉黑了“我”所有的联系方式,彻底消失在“我”生活的世界里,若干年之后,是否也会像怀疑老皇猫之死一样,怀疑江媛此人的曾经存在。
张烨:这期青年专辑中,我认为在小说“技法”上最游刃有余的就是《猎人之死》。小说以追寻记忆中老猎人为主线,记忆的不稳定性,带来的是“我”存在的不确定性,这其实跟“我”的现实处境有关。如此,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小说开头设置了一场大雨和面试。偶然的大雨让本来处于劣势的“我”得以顺利入职,可以想象,一个偏远乡村来到大城市打拼的青年,生存境况并不会很轻松。漂泊青年在感情空虚之下,只是跟江媛的初次约会之后,就“憧憬着我们的结合”。老猎人的捕猎技巧仿佛就是“我”生存的隐喻:老猎人谈及何为好猎人,他的诀窍是“要骗”,他说,“给它甜头,让它自愿跑到陷阱里,再照头开枪。”再回到现实,“我”突然发现,她其实从未向“我”开口借钱,每次都是“我”主动向她转账并劝她收下。那段时间施予的快感令“我”上瘾。——于是,老猎人-猎物;江媛-“我”构成了相互的隐喻,老猎人的三种死亡隐喻着“我”对现实的捉摸不定。青年漂泊者的命运犹如小说中的“记忆迷雾”,以至于他洞穿自己的生活不过是一场骗局之后,是执拗地相信自己更了解自己活过的时间,还是将“原以为失去的纠正为从未拥有”?
《猎人之死》未必是专辑中立意最深的,却是通过文学的形式,将自己想要说的事情,表达得最好的一篇小说。小说通过几个颇具趣味的设置,比如老猎人死亡的谜题、阅读期待的错置、“我”叙事的可信度和翻转,这些地方都让小说颇具匠心。《猎人之死》也是专辑中表达最为节制的一篇,我觉得这点颇为重要,太多“感觉”让读者怀疑故事的可信度,《猎人之死》在技法上的成熟让小说变得有趣和可信。

穆萨
王玮旭:张烨提到几篇小说的经验“深度”与叙事“技术”的问题,佳颖则注重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分野,讨论了小说的形式特征。从主题上来看,“自我”的认知和建构及其困难可以说是三篇小说共同的主题,张烨看到《七伤拳》中每个人的自我都戴上了假面,结果是每个人的自我都难以自洽;佳颖看到《爆破游戏》中人物自我的虚伪和弱点;雨昕关注小说中人物的“虚无”处境与“成长”的可能性,王子睿似乎是几篇小说中唯一一个有可能走出困境的人,但是必须以某种程度的虚无主义为代价,似乎也偏离了曾经的“自我”。三篇小说从不同的角度言说了一代人的成长之难,引人深思。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