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新见陈寅恪旧诗二首》(载《上海书评》2024年7月19日)发出后,文辉兄撰《关于凌道新所抄陈寅恪诗》一文(载“历史的擦边球”公众号2024年7月26日),表达了不同意见。文辉兄的观察自有道理,同时促使我深入思考,在无铁证史料前提下,断语应格外审慎,这样才可深入判断我们遇到的学术问题。他的疑问提醒我,判断新见陈寅恪旧诗需多方思考,仅凭文字差异匆忙结论,或许会误导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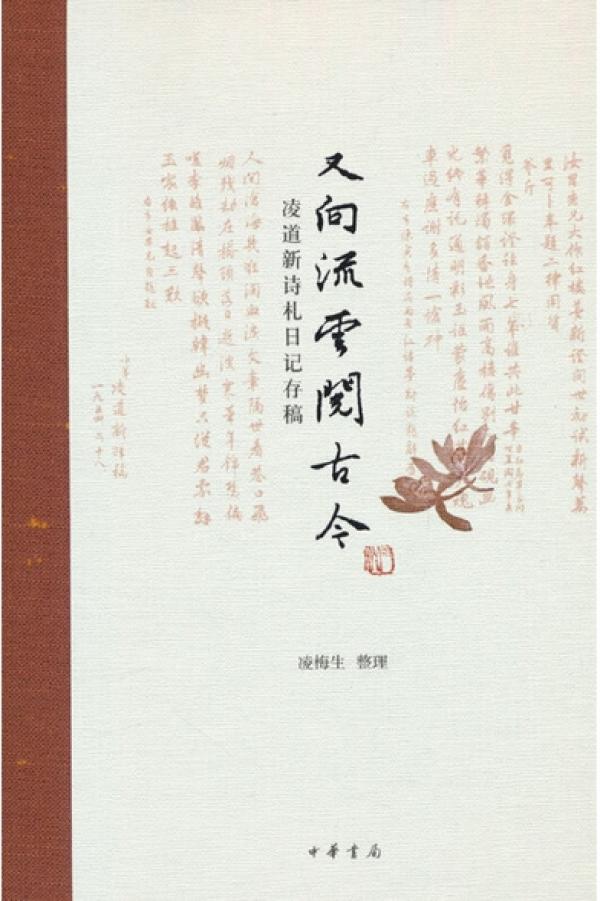
《又向流云阅古今:凌道新诗札日记存稿》,中华书局版
文辉兄的判断是二诗非陈寅恪手笔,大概率是凌道新一时兴起,代陈“重写”。理由一是凌道新和吴宓过从甚密,凌对陈诗的了解应来自吴,而吴并无此陈诗文本;再是凌当时处境不可能获得陈诗,即令获得,吴也会知晓并一起分享,而吴书中不见此文本;三是凌具相当旧诗功底,有能力“重写”。我在文辉兄的启发下,进一步思考,感觉凌抄陈诗确实还有讨论余地。
凌道新年谱将二诗系在1969年和1972年下,所据是抄录时间,非写作时间。这样二诗实际写作时间就成了关键问题。因抄本无题及日期,我们只能从诗意推测,第一首:
鸡林鸭绿阵云深,谁启开边武帝心。
汉腊只余残烛夜,楚氛翻作八方阴。
烦冤新鬼家家梦,破碎河山寸寸金。
剩有宣和头白老,岭梅如雪对哀吟。
此诗源自1945年陈诗《玄菟》,全诗如下:
前朝玄菟阵云深,兴废循环梦可寻。
秦月至今长夜照,汉关从此又秋阴。
当年覆辙当年恨,一寸残山一寸金。
留得宣和头白老,锦江衰病独哀吟。
第二首诗题《与公逸夜话用听水轩韵》,全诗如下:
昨夕阎浮色变空,众生形解动刀风(刀风解形,语出晋译修行道地经)。
东飞帝子冤成鸟,南伐军人惨化虫。
细柳一般兵作戏,大槐何日战方终。
皂罗今岂长安有,愁杀鸡群老秃翁。
此诗源自1945年陈诗《十年诗用听水斋韵》之三,全诗如下:
金谷繁华四散空,但闻啼鸟怨东风。
楼台基坏丛生棘,花木根虚久穴虫。
蝶使几番飞不断,蚁宫何日战方终。
十年孤负春光好,叹息园林旧主翁。
陈诗此题亦见于吴宓日记及存稿,题作《与公逸夜话用听水轩韵》,全诗文字略异。不抄。
凌抄二诗,虽句句用典,但并不生僻。第一首“鸡林鸭绿”语意双关,即朝鲜和鸭绿江,可判断此诗约作于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后(1953年停战前)。“鸡林”是旧诗习语,陈寅恪常用,《元白诗笺证稿》开篇即言:“此无怪乎压千岁之久至于今日,仍熟诵于赤县神州及鸡林海外‘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也。”《柳如是别传》第五章引《列朝诗集》“朝鲜门”中“许妹氏”条中语:“岂中华篇什,流传鸡林,彼中以为瑯函秘册。”(三联版,1004页)。第二首中“细柳、南阀”典故,在旧诗中多与战争相关,其他典故也多涉战争及人民苦难,“宣和头白”“岭梅如雪”等,均为陈诗习见语词。“刀风”属僻典,前已指出,陈寅恪1951年5月《首夏病起》亦有“刀风解体旧参禅”句并有自注:“晋法护译禅经,详论人死时刀风解体之苦”,凌抄本注“刀风解形,语出晋译修行道地经”,更具体,异诗同典出注,如此巧合,似出同一人之手。
吴宓日记中虽曾大量抄录陈诗,但据此难说吴书未录即非陈诗。吴抄录陈诗有特殊时代背景,1951年秋,吴曾因别人告发,私信检扣,所作旧诗被认为对土改和新时代不满,受到过有关方面指控,所以他在抄录友朋诗稿时格外谨慎,有些诗意明显的作品,或许会作保留。直到1959年12月9日,吴宓致金月波信中还说:“宓旧友惟陈寅恪兄仍有旧诗寄示,而如武汉大学之刘永济兄、何君超兄,均已不作诗词,且责宓之改造尚不足云云。”(吴学昭整理《吴宓书信集》,328页,三联书店,2011年)
凌道新虽具旧诗功力,但他在1969年及1972年间,“重写”陈诗的心理何在?况且还是“重写”两首关于战争的诗,虽说事过境迁为诗并非绝无可能,但以常理推测,在当时处境下,作者忽对战争大发感慨,其中诱发因素何在(“珍宝岛事件”倒是在这个时间,时地近似,或可进一步研究)?二诗皆为次韵之作,依旧诗习惯,如出凌手,明确标为次韵并不失个人创作意味。再者,凌在鸣放发言中依然承认“党和政府的这种大开言路的贤明作风,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党之威信无比崇高,全国人民对党衷心拥护,已为确定之事实”(《凌道新先生的发言》,载中共西师委员会宣传部编《学习简报》第3期第3版,1957年5月28日),虽有陈诗旧作在前,但写出“鸡林鸭绿阵云深,谁启开边武帝心……烦冤新鬼家家梦,破碎河山寸寸金”这样的诗句,也超出我们的想象。
期待将来有机会发现二诗原始文本,或其他不同抄本, 同时也期待凌家后人妥为保存相关原始文献,以备来日大家共同依原物判断。最后说一句,二诗无论出陈出凌,在那样的时代下,都是难得的好诗。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