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名相张华是中古政治史绕不过去的人物。他颇为传奇的仕途与灭吴、立储、贾后崛起及司马伦篡位等众多政治大事件交织。其卓越的文学造诣和出色的行政能力也构成了传世文献中的“史相”之主体。在愈发阶层固化的魏晋士族时代,张华凭借才学和政治素质从相对贫寒的家世中脱颖而出并位极人臣,实属不易。但其家族的富贵荣华却也止于张华一代。在张华和两个儿子命丧司马伦之乱后,尽管其孙张舆任职于东晋新政权,但终晋、宋、齐三朝该家族再无人丁仕宦显达。虽然张弘策曾以“梁武帝心腹+从舅”的开国功臣身份重振门楣,但他的政治成功毕竟有太多勋戚色彩,与建康文化士族的格调全然不同。琅琊王僧孺在6世纪初新修《百家谱》时才把张华和张弘策所在的范阳张氏纳入名门行列。这也从侧面说明张华-张弘策一系在东晋南朝的境遇较其他侨姓士族相距甚远。而张弘策的后代至唐初也基本绝迹。
然而,即便张华的直系后代家道衰落,但这位魏晋名宦的史相,尤其是突出“文”的那一面,却成为唐代很多张姓寒门借科举崛起后宣告自己“士族”地位的文化资源。张说、张九龄、张嘉贞和张柬之四个张姓宰相家族皆在不同时期冒认或被误认为张华的直系后代。这一现象是张华留给历史的一条长长的背影。随着唐代科举逐渐促进阶层流动,这个背影显得尤为醒目。
张说
我们先从唐玄宗时期的著名政治家燕国公张说说起。在他波澜壮阔却也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中,几乎每一个步点都踩在了历史进程的脉搏上。尽管张说出身寒门,家族世世代代在体制边缘与下层官僚间辗转,但他成长的年代却恰恰迎来了唐代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关键变革期。从武则天的崛起到唐玄宗的开元天宝盛世,这近百年间见证了唐代科举制的愈发完善以及统治者在选官上对文学才华的愈发重视。中国科举史上的第一场殿试即由武则天亲自主持,作为女皇登基前夕的盛大政治工程。时年23岁的张说则以绝伦天赋一举夺魁。几乎于一代间变寒门为士族的传奇人生也肇始于此。
张说三秉大政,四上疆场,在政治与军事上都立下赫赫之功。从大历史的角度审视,他更是主导了几项对唐宋制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变革,尤其是推动府兵制向募兵制转型的改革。此外,他还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这一举措在唐宋皇权螺旋式上升、君主逐渐走向台前的大趋势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张说本人和当时及后世的吹捧者们在塑造其形象时似乎都更重视更为纯粹的“文治”一面:作为不世出的大文豪、“大手笔”,张说有着四掌纶诰、三修国史的华丽履历,更是在发展书院体系,修撰重要文教图书等工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科举文化逐渐蔚然成风的时代,通过科举入仕的文学才子们会策略性地在塑造事功卓著的名臣形象时更偏重文治。这种建构旨在进一步加强统治阶层对文学才能的重视。陆扬在《清流文化与唐帝国》一书中甚至认为张说自己就曾策略性地把上官婉儿的形象“制作”成一名以文学才华治理天下的女宰相。受张说提携且同为科举入仕的张九龄和孙逖分别用“公之从事实以懿文”和“海内文章伯,朝端礼乐英”形容他的政治生涯。
在张说建构门第时,作为魏晋文豪的张华也因此成为了极具战略价值的文化资源。按照唐代精英社会的标准,张说门第低微,他的儿子们虽然享受着父亲带来的荣华富贵,却无法摆脱同僚们眼中“暴发户”的刻板印象:“以燕公张说为近代新门,不入百家之数。”(《封氏见闻记·卷10》)
现存的张说父辈及祖先的最原始的家世记载皆出自张说本人之手,来自于他撰写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的三方墓志。这三方墓志皆称其家族为张华的直系后代。张说在曾祖父墓志中对张华后人的记载却与基本史实矛盾,暴露了其伪冒家世攀附张华的嫌疑。墓志称张华的儿子张祎为避五胡之乱而渡江,六世孙为太常,然后迁徙至河东(即张说的老家):“司空生祎,避胡过江,六世至太常,而复寓于河东之族人。”但成文更早且更权威可靠的《晋书》则明确记载张祎与父亲同时遇害,过江的是张华的孙子张舆。在欧阳修所编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里,避胡过江的变成了张华另一个儿子张韪,但依然与史实不符,因为张韪也是和父亲同时遇害的。
张说建构家世的破绽不仅限于此。例如,他在曾祖父墓志中称自己有个祖先是张华的七世孙,一位迁徙至河东的南朝“太常”。在南朝,太常作为九卿之首,是极为清显的官职。若其在职时叛逃至北朝,应视为重大政治事件,却不见于记载南北朝的众多史料,这显得颇为奇怪。同时,南朝重臣叛逃后一般会在新政权获赏高官厚禄,但张说撰写的墓志对此却毫无体现,只是言其“寓于河东之族”,这并非墓志书写的常态,毕竟中古墓志通常对祖先职官较为重视,此处忽然言及河东反倒是露出了与张说祖籍河东强行联系的痕迹。若此“太常”并非叛逃,而是在隋灭陈后被带到北方,那么墓志所描述的情景在人口学上就显得尤为惊人。张华于公元232年出生,距隋灭陈有358年之久,却仅传7世,需要很多代人都出现“老来得子”的罕见情况才行。
种种与史实和逻辑不符的表述体现了张说伪冒家世的执著。事实上,张说建构谱系不止于张华一代。墓志中还声称张华是东汉司空张皓、西汉开国元勋张良的直系后代。然而,包括《后汉书》、《晋书》在内的众多成文比张说时期更早且更权威可靠的正史材料都没有记载过张华竟然还有这层家世。这种到8世纪初期才从张说笔下出现的说法意在构建一个连接两汉、魏晋和盛唐的超级张氏门第,涵盖了各时期的顶流张姓名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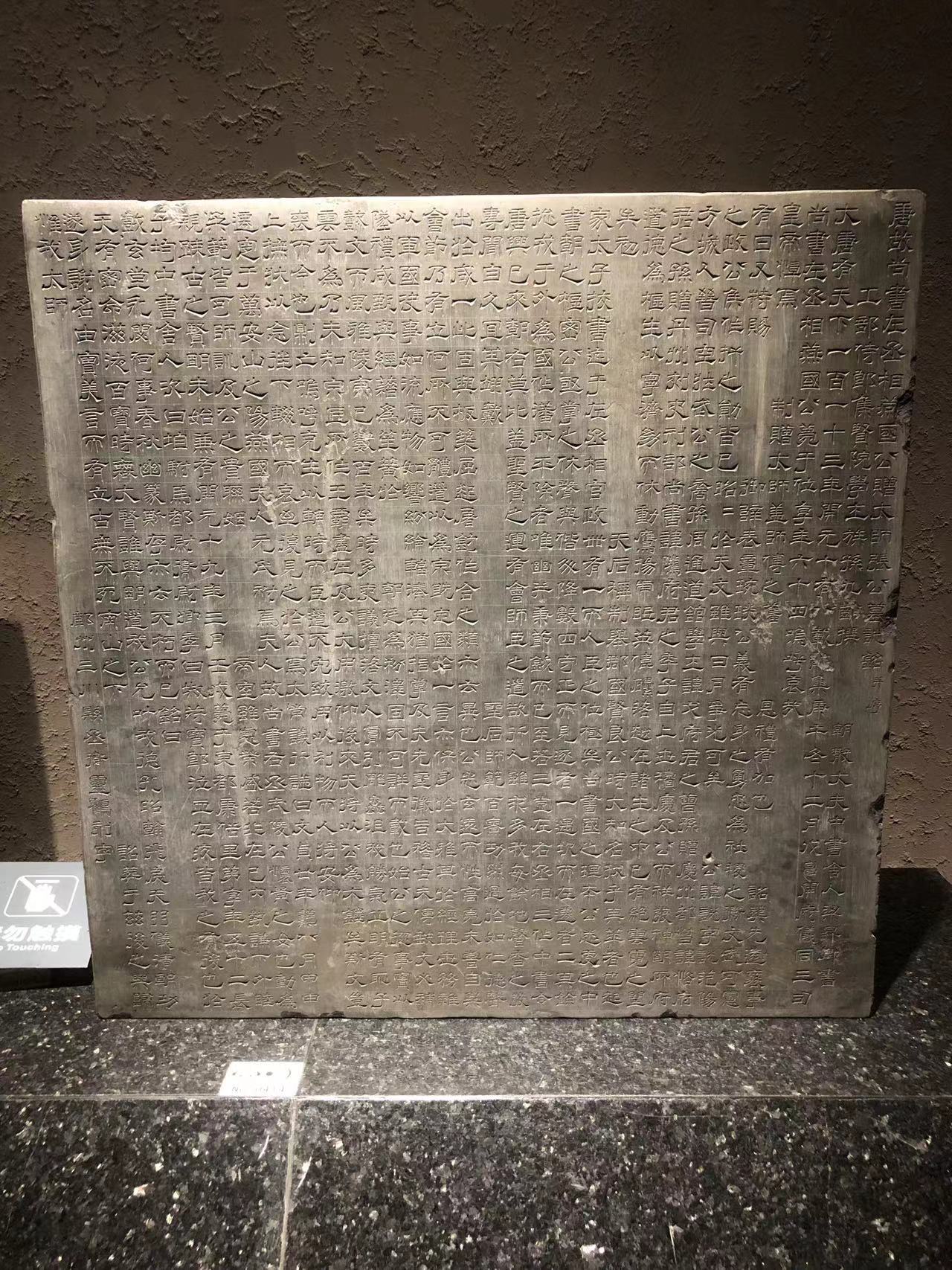
张说墓志
张九龄
作为另一位靠科举上位的寒门宰相,张九龄与同朝为官的前辈张说惺惺相惜,也是张说重点提携的政治盟友。张说的墓志即为张九龄所撰,后者也借此机会进一步深化了前辈作为“大手笔”的文宗形象,甚至将其打造为推动文学在唐代涅槃重生的复兴先驱。二张的“商业互吹”不仅是文坛佳话,也体现了科举文士们高妙的政治智慧。
张九龄出身于基层官僚家庭,自高祖至父辈为县丞、州别驾、县令、县丞。而韶州始兴又是帝国边陲的欠发达地区,在各种意义上都与以长安、洛阳为核心的王朝腹地相去甚远。无论从他自己还是同僚们的认知来看,张九龄都是名副其实的岭南寒门。在张九龄指责牛仙客出身低微后,唐玄宗甚至嘲讽张九龄:“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阀阅?”张九龄也不得不坦然承认自己是“岭海孤残,不如仙客生于中华”。牛仙客虽然是西河小吏出身,但家乡泾州毕竟依然在两京政治文化中心的辐射范围内,两汉魏晋南北朝不少名宦也涌现于此地。张九龄在信件中也坦言曾“居本海隅,始无朝望”,并艳羡那些“中朝著姓,连姻华族”的士族子弟。
科举制度为唐代的很多“草泽饱学之士”提供了阶层晋升的机会。一批又一批“寒门贵子”们在发迹后并不满足于物质和官阶上的社会流动。他们更试图动用作为文官所掌握的社会及政治资源彻底抹去自己的“新贵”身份,通过伪冒郡姓和嫁接谱系的方式把自己打造成旧族成员,自古以来便是贵胄。张九龄也不例外,但他的具体操作较为简单:既然前辈已经把路铺好,他只需和张说攀亲戚即可。因此,不仅正史中明确记载二张“叙为昭穆”,在现存张九龄所写的很多有关张说的作品中也能看到“族子”二字(在张说墓志里张九龄的落款则是“族孙”)。而张九龄兄弟的墓志也理所当然地称自己为“范阳”人。张九龄的外甥为其立碑时也沿用了张说的建构“成品”,把张良和张华对仗而称。白居易也在张九龄侄孙的墓志上强调其为张华之后。
需要强调的是,在二张伪冒祖先及嫁接世系时,张华及范阳张氏并非最直观的选项。当时显赫的张姓郡望还有清河、敦煌、吴郡和南阳。前面两个郡望都有世系明确的成员在7世纪时任显宦(清河张文瓘、敦煌张公谨),吴郡张氏则是非常具体的吴姓士族。冒认这三个郡姓可能会有较高“成本”,但南阳张氏则是直接可以用“拿来主义”获取的门第,并且在初盛唐声望颇高。(仇鹿鸣《制作郡望:中古南阳张氏的形成》)张说和张九龄却另起炉灶,正说明“张华IP”与科举时代张姓文士崛起的大势十分契合。
张嘉贞
终唐一世,364位宰相中虽然有22对父子皆宰相的事例,但祖父-父亲-儿子连续三代皆拜相的家族只有张嘉贞-张延赏-张弘靖一门。“三相张家”是体现科举促进中古社会流动的鲜活事例。这个唐代最辉煌的宰相世家并没有魏晋南北朝旧族那样的显赫门第,他们在8世纪以前还只是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姓。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三连冠家族恰恰是科举时代诞生的寒门新贵。张嘉贞在武则天时代以明经科考入仕,摸爬滚打后于唐玄宗时期拜相。他的儿孙张延赏和张弘靖则分别以父辈门荫入仕,最终也于德宗和宪宗朝接连拜相。
无论按照正史记载还是时人的理解,这个从寒门跃进至士族行列的张家一直以“河东”为郡望。张嘉贞的爵位就是“河东侯”。按照唐代传统,爵位名号所包含的地缘称谓往往是朝廷对获封者郡望的认知。子辈张延赏神道碑也称郡望河东。孙辈张谂的墓志上也显示其授封河东。甚至到了晚唐,张嘉贞的玄孙,“官五代”张彦远在著作《历代名画记》里亦称河东。10世纪成文的《旧唐书》也用“蒲州”这个与河东相对应的唐行政区划来形容张家的籍贯。系统地把该家族归为张华后代的现存文本是11世纪中叶才形成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下称“《世表》”)。该表声称张嘉贞高祖张吒是张华“裔孙”,在隋朝从范阳因官迁徙至河东。这个很晚才出现的说法颇为可疑,毕竟如上文所述,张华与二子同时被害,只有孙子张舆幸存而逃至江南,范阳本家依然有余续尚存的概率不高。再加之《世表》在此前介绍张韪、张祎时就已经犯过错误,张嘉贞是范阳张华后代的说法可信度很低。
具体为何张嘉贞家族在10世纪以来逐渐被嫁接至张华谱系之下我们不得而知,但张嘉贞弟弟张嘉佑的墓志曾称“范阳人”,这也许是谱系建构者和编纂者的“灵感”来源。张嘉佑墓志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成文,刚好在张九龄去世后两年。张说则在开元十八年冬(公元731年)去世。也就是说,张嘉佑墓志成文的年代恰恰处于两个生荣死哀且留下厚重文化遗产的“范阳”张氏宰相之“余震”中。张华这一“IP”在张说和张九龄的双重炒作下显得格外光彩。张嘉佑墓志受此影响也是有可能的。有趣的是,张说领兵时还曾是张嘉佑的老上级,按照后者墓志记载:“还并州司马,副燕公军使经略太原。”
但到了张嘉贞的子孙辈张延赏、张弘靖之时,他们已经连续两代、三代官拜宰相位极人臣,“河东张氏”俨然成为新的门第,恐怕已经有了不再需要嫁接、挂靠到范阳的“文化自信”。若9世纪流传的说法为真,那么张嘉贞家族在崛起后的第二代就已经牛气到不愿与家世有些许下滑的北朝旧族联姻了。这个“不识韦皋是贵人”的河东宰相世家,在当时是没有太多理由继续借用他人郡望的。更何况在8世纪中期因为张说二子张均、张垍于安史之乱失节投敌的缘故,范阳郡望出现了“劣迹”。另一支冒认范阳的张姓家族,唐肃宗张皇后家族,据仇鹿鸣的推测,也是在8世纪中期放弃了范阳郡望而改宗南阳。
张柬之
科举文士策略性冒认张华后代的模式并非适用于所有存在谱系嫁接嫌疑的张姓寒门家族。这里要谈到另一位张姓寒门宰相张柬之。这个在神龙革命中推翻武则天政权的主要功臣来自中下层官僚世家,父亲是益州府功曹参军,祖父仅为隋朝县令。张柬之和稍后涌现的张嘉贞、张说、张九龄等后辈一样,都是靠科举上位的寒门子弟。张柬之家族没有采用冒认的策略,却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被误认为张华之后。若不假思索地阅读张柬之家族历代墓志上的表述,我们可能会误以为其与张华的血统联系是该家族成员历代“层累”构建谱系所致。但更深入地分析表明,这种联系可能只是欧阳修在撰写《世表》时的一记“乌龙”。
《世表》认为张柬之是张华的后代,而这个谱系的关键衔接是张弘策。张弘策在正史中被明确记载为张华后代,且世系清晰,并没有与史实相矛盾之处。而且张弘策家族在梁初也被时人认为是张华的直系后代。(梁武帝:“张壮武云‘后八叶有逮吾者’,其此子乎。”)那么如果张柬之与张弘策的血统关系为真,则张柬之与张华的血缘联系也就有相当高的可信度。
《世表》对张柬之父祖的记载与该家族出土墓志描述基本一致,而按照《世表》的说法,张柬之祖父与张弘策之间只隔了一层曾祖父“紑,后周宣纳上士,隋巴州录事参军。”这里问题有二。首先,《梁书》、《南史》等成文更早且更权威可靠的史料以及《资治通鉴》这种依赖成文更早的史料的史学作品并没有记载张弘策有名为“张紑”的儿子。当然,这里不排除有史书遗漏的可能,也许“张紑”没有鲜活事迹值得留名于正史文献。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张弘策在公元502年就去世了,而这个名叫“张紑”的儿子,根据《世表》的说法,至少在公元581年(隋)还在做官,甚至终官于蜀地巴州。假使“张紑”在张弘策47岁去世的那年才出生,那么他也活了80个年头。80岁依然在巴州任参军并非概率为零,毕竟张柬之自己在81岁时还位极人臣。但在中古社会连续出现两代高寿老人确实很罕见。更何况从隋朝的出土墓志可看出,张弘策有很多直系后代的自然死亡年龄并没有太过离谱。曾孙女张贵男在公元605年去世,享年56岁;孙子张盈在601年去世,享年58岁;孙女张娥英在612年去世,享年64岁;孙子张軻在614年去世,享年68岁。
《世表》的记载虽有不寻常之处,但探究此事还有赖多方出土的张柬之家族墓志。目前出土的相关墓志共11方之多,历经数代。若初观墓志,读者也许会感到明显的“层累”建构之痕迹。张柬之的兄弟庆之、景之和敬之三人的墓志均由张柬之本人于周天授三年(公元692年)撰写。张柬之还参与了父亲墓志的撰写,虽落笔时间不明,但考虑到墓志言及在唐末周初父母均已入土,最终成文时间应该不会在7世纪之后。这四方墓志都可视为张柬之这代族人在8世纪之前书写家世的一手文本。在这个文本里,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对张弘策(以及张华)的提及,虽然墓志声称郡望为“范阳方城”。
直到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墓志文本里才出现了看似是声称自己为张弘策后代的表述。这一年下葬的三方墓志的主人分别是张柬之儿子张漪和孙子张軫、张点。文本中都出现了一个南北朝时代名为“策”的祖先。而另一个提及先祖“策”的文本是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成文的张柬之曾孙张曛墓志,志文表明张“策”的儿子是“周宣纳上士,隋巴州录事参军”,与《世表》说法相吻合(虽然墓志里这个儿子名“玠”而非《世表》中的“紑”)。现代学者也认为家族墓志中出现的“策”就是张弘策。(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
但若真的把志文中的“策”当做张弘策,就会有多个指向层累伪冒家世的“证据”。如前文所说,张柬之是张弘策后代的说法在8世纪前并不存在,张柬之亲手书写家世的三个作品也都没有此说法。该说法是在733年才出现的,并在9世纪初更加深化。而更明显的证据则是该说法有两处与基本史实不符。首先,张弘策本人明明是在公元502年坚守卫尉府时被作乱的南齐余党杀害,这是南朝政治史上的大事件,而8世纪和9世纪的墓志文本却都说张(弘)“策”加入了公元535年才建立的西魏政权。这个历史错误非常离谱。其次,多方墓志提到张(弘)“策”的祖先是一个从北方迁徙至南方政权的名叫张“贞”的人,但这也与成文更早且更权威可靠的《梁书》、《晋书》等正史记载不符。张弘策的南迁祖先是张华的孙子张舆,而非张“贞”,《梁书》在这方面的记载洽可以与《晋书》张华本传对后代存活情况的记载相对照。另外,如上文所述,隋朝时期有一些可以确定为张弘策后人的墓志下葬,而这些成文更早的墓志则根本没有提到张“贞”这个人。种种与事实和逻辑不符的现象使得“张柬之为张弘策后代”的说法难以成立。
然而,在推翻这个说法后,我们真的能确定张柬之后人是在主动“伪冒”家世,主动造假以便认祖张华么?这似乎也说不通。首先,随着张说、张九龄等科举文士在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双重成功,张华确实成为了盛唐时期的顶级IP。但按照此逻辑,张柬之孙辈们在把世系嫁接到张华的直系后代张弘策一脉后,应当在同一方墓志里借机猛提张华才对,但声称张(弘)“策”为祖先的文本里都没有在描述家世部分对张华进行任何提及。如此费力“挂靠”在张弘策之后,却丝毫不提真正的大IP张华,难道张柬之后人真的那么笃信古代读者们的思维跳跃能力和历史知识水平?其次,即使退一步讲,张柬之后人并没有那么在乎张华,他们只是想冒认一个历史名宦为祖先,那么作为梁武帝开国元勋且官拜卫尉卿、散骑常侍等显赫职位的张弘策确实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张家墓志对张(弘)“策”的官职表述却又完全不是这个路数。目前所见的最详细表述是“梁岳阳王谘议参军”,来自张柬之曾孙于元和八年(813年)下葬的墓志。梁岳阳王是萧詧。皇子谘议参军这类职位只是中层官职。非但张弘策本人从未担任过梁岳阳王的谘议参军(这也是“张柬之为张弘策后代”之说法无法成立的另一原因),即便他担任过这个职务,为何张柬之后人不把他更高的卫尉卿、散骑常侍写进墓志,而反而留下一个中层职务?这既不符合墓志的文体也不符合造假的动机。可能读者看到这里会不禁发问:张柬之后人到底是从哪里拿到这么一个让公元502年殉职的张弘策担任公元531年之后才授封岳阳王的萧詧之部下的“秘本”?张柬之后人又是因为什么非要选一个中层官僚当假祖宗?
既然“张柬之为张弘策后代”这种说法有太多漏洞,但主动造假之说又不合常理,另一种更有可能的情况浮出水面:张柬之后人并没有造假,他们的祖先确实叫“张策”,而非张弘策。要知道唐代的避讳制度并没有严苛到在盛唐和中晚唐都不能用章怀太子李弘的“弘”字的地步,毕竟上文的张“弘”靖就没有改过自己的名字。若张柬之后代真想造假,大可直接用“弘策”二字,而不是在所有提及这位祖先的墓志里都只提“策”不提“弘”。同时,8、9世纪提及张策的四方墓志有着非常一致的表述。开元二十一年的张漪墓志称张策从“后梁宣帝入西魏”,这与元和八年的张曛墓志“梁岳阳王谘议参军”完全吻合,因为梁岳阳王正是后来的西魏傀儡政权(后梁)国主宣帝。开元二十一年的另外两方墓志分别写道“随梁北归”和“去西魏自南齐”。后者虽然犯了齐梁混淆的错误,但这四方墓志总体来看所言皆是张策在萧氏政权任职并最终随该政权归入北朝一事。萧詧向西魏称藩并彻底成为傀儡政权之主的时期大概比张弘策去世晚将近两代人,那么如果“张策”活跃于此时,他的儿子到隋朝开国时应该在40-60岁左右,不需要完成像《世表》中误记那样“80岁还要在隋朝蜀地做官”这一挑战人口学原则的任务。
在排除了张弘策后代和主动造假两种可能后,张柬之后人真实记载祖先的可能性就非常高了。这样一来墓志中那个从北方南迁的“张贞”的存在也与《梁书》对张华-张舆-张弘策一系的记载没有冲突,因为从张贞到张策再到张柬之,这一支本来就和张弘策一系毫无关系。而张柬之家族墓志所称的“范阳方城人”可能只意味着他们最初也是来自范阳的张姓家族,他们的远祖张贞与张华应该没有很近的血缘关系,毕竟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攀附张华。
在这批墓志之后,我们再一次看到详细记载张柬之家世的文本便是欧阳修所编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了。把张策和张弘策混淆也许只是欧阳修的原创错误。但这记“乌龙”可能也反映了9世纪以来的政治及文化发展。或许是这些发展让张柬之一系逐渐被认为是张弘策的后代。或者是这些发展让张柬之的后人们自己更愿意把祖先往张华方向靠拢,若真如此,那么利用张弘策是张华真实后代这一得天独厚的“资源”,把张(弘)策与张策混淆则是物美价廉的策略。随着中晚唐时期科举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以及唐廷在藩镇时代对刻画自身合法性和神圣性的极度重视,统治者对文学才能的渴求愈发强烈。另一方面,科举擢第-翰林学士-宰相的升官途径也愈发制度化、清晰化。与此同时,带有南北朝色彩的职官清浊分野似乎在9世纪有死灰复燃之势,而中央文官在这个潮流下毫无悬念地成为了士人们追求清显的首选。与这些制度发展互为表里的则是以翰林学士为内核的词臣群体在掌握政治“笔杆子”后对彼此及属于广义清流序列的科举文士的吹捧,旨在进一步巩固这些符合自身政治利益的文化趋势。(见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科举功名的政治和文化价值也因此达到空前高峰,甚至演变为一种足以替代且超越门第以证明自身精英属性的“资质”。在词科文化的霸权支配下,文治形象鲜明的前史名宦在寒门冒认郡姓的“市场”上只会更加炙手可热。前文提及的张皇后家族在8世纪中期放弃范阳郡望后又在9世纪将其重新拾起,而“著博物于晋朝”的张华当然也在这次建构工程中跃然纸上。(《唐故检校少府少监驸马都尉赠卫尉卿范阳张府君墓志铭》)若张柬之后人亦受此气候影响则不足为奇。
张华出身寒门却“伏膺典坟,俯拾青紫”的奇迹在九品中正制日趋完善的东晋南朝变得更加难以复制。但他长长的背影却随着科举在唐代的制度化而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门非世胄,位以艺升”在唐代早已是稀松平常之事,杨收、曹确、毕諴、刘邺、刘瞻、归登、归融、归仁晦、舒元舆、卢肇、王起等凭科举上位的新贵更是在9世纪如雨后春笋般到来。魏晋南朝不属于张华,但盛唐以降却是张说们的时代。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