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其实是一座‘叛逆之城’——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上,那些‘经典’的法国美学都不见了踪影,因为巴黎的经典本身,就是经过一次次叛逆的革新建立起来的。”
巴黎奥运会落幕不久,作家张佳玮的最新随笔集《巴黎,生活在此处》恰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
张佳玮曾在巴黎,饶有兴致地走遍大街小巷,作为一个“外乡人”,好奇地打量过这座“流动盛宴”的大小转角:被誉为“文学乌托邦”的莎士比亚书店、记录了印象派的传奇的奥塞博物馆、作为1920年代贫穷艺术家栖息之所的蒙帕纳斯、左岸的咖啡馆和右岸的奢华酒店……
今年上海书展·上海国际文学周期间,张佳玮在上海,与读者分享他在巴黎的所见所闻,于细微处体会一座叛逆而多元的“乐活之都”。

“巴黎综合征”:繁华抑或落魄
张佳玮的分享以一个流行于1980年代日本的现象开头——“巴黎综合征”。它源于泡沫经济时代日本游客面对想象中的浪漫之都与现实的巴黎之间的强烈落差,而后被应用于各种类似场景。
巴黎为整个世界留下了太绚丽的幻影,仿佛那里只存在着无数艺术家和他们的杰作、无数浪漫的邂逅以及数不尽的荣华富贵。可是等待他们的也许是满街的马粪、糟糕的治安和爱搭不理的巴黎人。
这种两端的差异在塞纳河左右岸也有所体现,张佳玮说,塞纳河左岸固然有名,花神咖啡馆、双偶咖啡馆、莎士比亚书店鳞次栉比,但历史上,左岸的顾客,大多是还未成名的艺术家和囊中羞涩的学生们;相比之下,右岸的卢浮宫、杜伊勒里花园、香街与丽兹酒店则是极尽奢华,代表着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值得一提的是,丽兹酒店正是1920年代出版了《了不起的盖茨比》,春风得意的菲茨杰拉德下榻的地方,也是可可·香奈儿去世的地方。
戏剧性地,当时还是“穷光蛋”的海明威就住在对面的左岸,并且因为自己的贫穷感到无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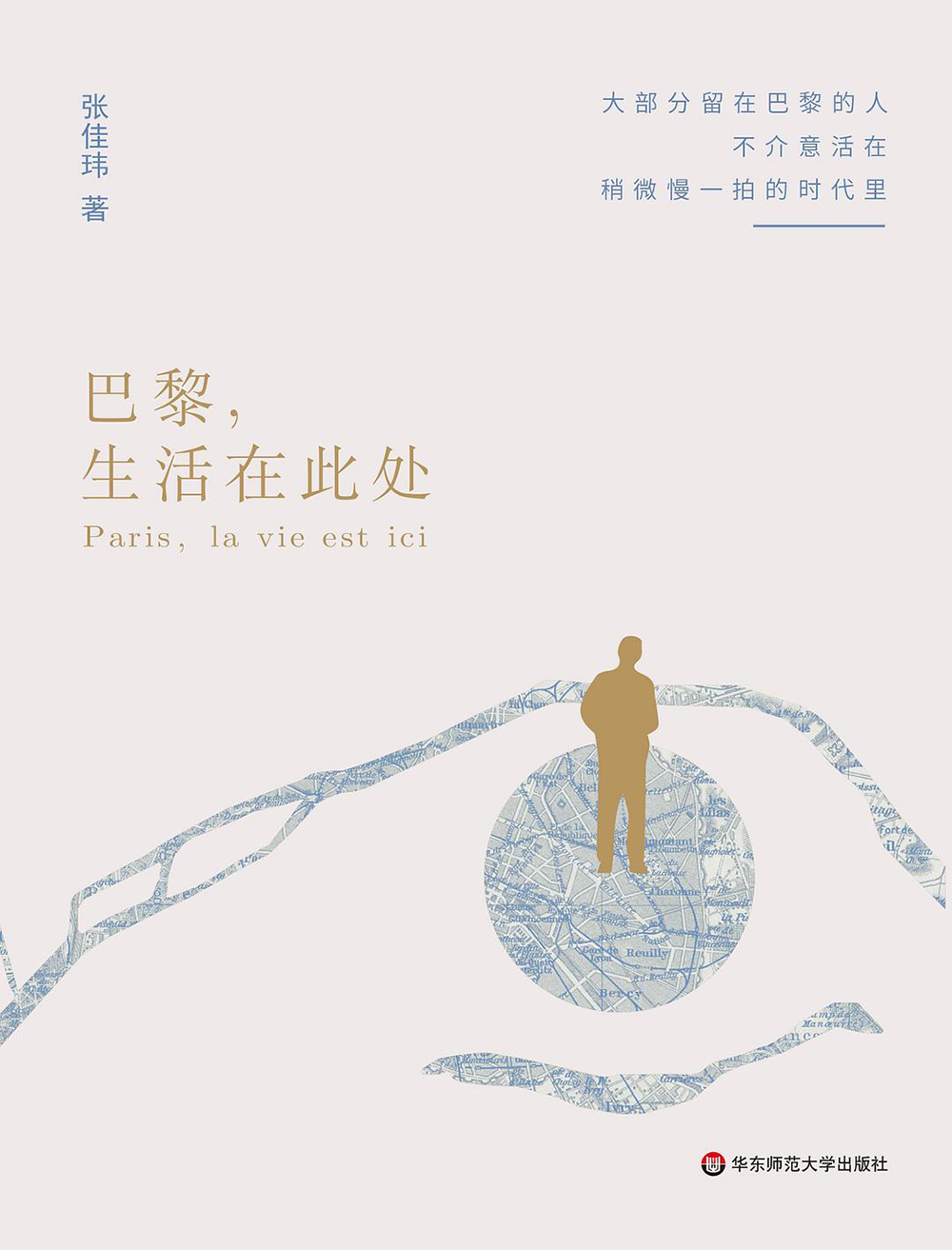
作为“叛逆之城”的巴黎
巴黎的“经典”形象过于深入人心。张佳玮以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为例,解释为何巴黎是一座“叛逆之城”。
比如,在印象派还未成气候的19世纪六七十年代,莫奈、雷诺阿等年轻艺术家,用自己独特的风格举办了画展,却被骂得狗血淋头,被冠以“印象派”之名”。马蒂斯和他的“野兽派”之名,同样来源于评论家的嘲讽。但这两种流派,如今都被写进了艺术史。
类似的,现在巴黎最有名的蒙马特高地,以及地标性的红磨坊之所以成名,是因为19世纪中叶巴黎改造,房价飙升,艺术家们面对飞涨的房价,只好集体迁居到北部的山上。在那里,糟糕的生活条件不能阻碍他们对率性生活的追求,被视为“低俗”的康康舞就起源于此。到了20世纪,这些都被奉为经典。同样的循环再次发生,而新一批艺术家,又扎堆去了蒙帕纳斯。
张佳玮说,作为一座用石头和砖块建立起来的城市,钢铁玻璃建筑在19世纪用于拱廊,到1900年巴黎世博会之后却成为主流,用于大小皇宫,被广泛地应用于现代建筑的构造和装饰中。在1920年代装饰艺术兴起后,这一风潮也远跨重洋,传播到了上海外滩万国建筑群。因此,在张佳玮看来,巴黎的“经典”正是在于不断的“叛逆”与革新。

属于“外来者”的城市
当然,对于在巴黎和上海都长期居住过的张佳玮来说,巴黎远不止于此。
在读者交流互动环节,一位来自上海的读者问张佳玮如何看待上海与巴黎这两座城市的气质异同。张佳玮引用了中国近代史中“冒险家的乐园”这一概念,指出上海作为彼时的“东方小巴黎”,与巴黎一样都是一座敢于突破常规、推陈出新的城市。
而这种精神正是伴随着城市对于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外来者的包容成长起来的。
可是一座城市如何体现TA对外来者的包容?
“拎得清。”张佳玮说。尽管上海人常被诟病“太精”,但这本质上是一种“各自安好”的边界感。在上海和巴黎,奇装异服者不会被过度围观,一个人甚至可以一周不与人交流地生活下去。同时,这种“不近人情”背后还有一份独属于现代社会的规则意识。
“每一个外来者都可以在上海和巴黎自顾自地生活,等他们习惯了,自然就成为了这里的一份子——在这里,大家都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过好自己的生活’。”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