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厌倦了贞洁又郁闷的日子,又没有勇气过堕落的生活。——波伏瓦
很难将马尔克斯的作品与波伏瓦这句话联系在一起,然而读完这部名为《我们八月见》的大师遗作后,我首先想到的便是这句话。它如此忠实地告诉我,要信赖自己的直觉,正如马尔克斯所做所写的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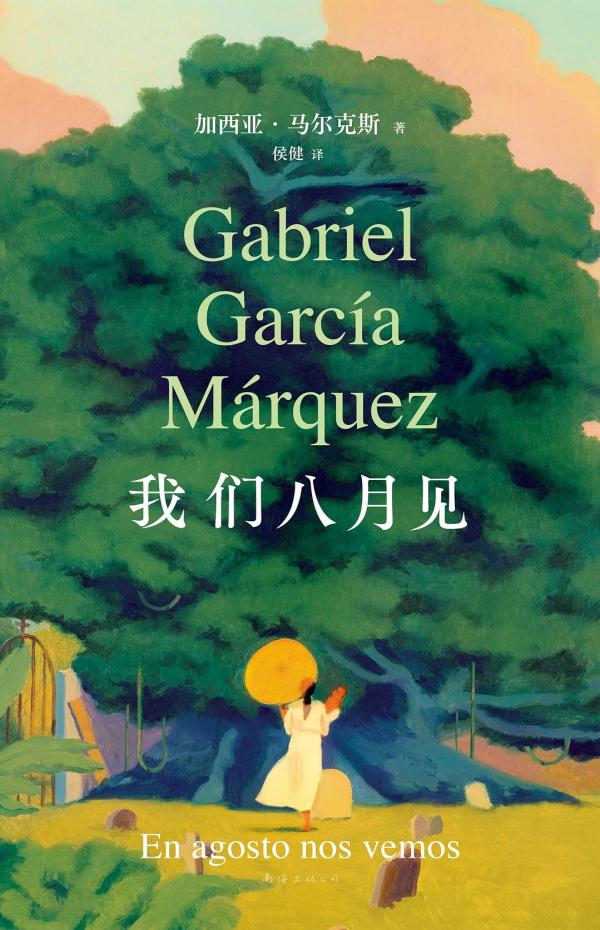
《我们八月见》书封
这本书创作期间,作家正承受着两种致命打击:一是来自年龄的背叛,年老记忆力的衰颓;二是他一生热爱的母亲去世了。很自然地,它们会被纳入作家创作背景的重要因素中考量。
“记忆既是我写作的原材料,也是我的工具。没了记忆,就什么都没了。”马尔克斯如此说道。因此,作家在生命的垂暮时刻来临时,在眼见着记忆逐步碎片化乃至行将消失的时候,创作了这部小说。对作家而言,没什么比丧失记忆更恐怖的了。没有记忆等同于没有作品。

《活着为了讲述》书封
有人说作家的一生都在书写童年,恐怕未必准确。不过,作家在即将丧失记忆的时候,他所想创作的主题毫无疑问是最为热爱的。马尔克斯在自传《活着为了讲述》中写过这样的话:“总之,和仆人们亲密无间,使我和女人心意相通,一生中,和女人在一起总是比和男人在一起更自在,更有安全感。我坚信女人支撑世界,男人只有捣乱的份,有史为证。”他热爱女性,创作了数不清延续世界的、稳定的女性形象。这部遗作的主角就是一位名叫安娜·玛格达莱纳·巴赫的中年女人(名字太长,我们姑且称她为安娜)。
安娜出场的时候,已经45岁,正如自传中作者母亲出场时的年龄。安娜在炎热的八月来到某个海岛,她从容地到了某个酒店,然后脱掉衣服,站在镜子前欣赏自己的身体——这里突出的身体器官是乳房,毫无疑问带有性暗示以及母性的隐喻,正如她已经是两个孩子母亲的身份。看到这里,几乎以为她等待的是情人,这是一个寻常的情人约会故事。
然而,马尔克斯以一个大师的手笔,跟我们开了个玩笑。他让这个美丽的中年女人在欣赏完自己还算完美的身体后,收拾整齐,走上街,走到人群中,买了一束剑兰。她确实是要约会,可是约会的对象不是男人,而是女人。不是生者,而是死者。原来,她是来给母亲扫墓的!
母亲临终前执意交代要将自己安葬在这里,家人只能从命。于是,每年的忌日,安娜都要来到这个小岛,然后在这里度过孤独的一晚。
扫墓完毕后,她真正的冒险之旅才开始。在酒吧里,她遇到一个很有眼缘的男人,他们彼此试探,愉快交流。很快,在酒精的作用下,她那个埋首于幸福婚姻生活中的被压抑的另一个自我开始逐渐苏醒。她有一个几乎完美的家庭,夫妻恩爱,可是她除了丈夫以外,还没有尝试过别的激情。这个念头让她跃跃欲试,她“厌倦了过贞洁而郁闷的生活”。她甚至一改平时的性格,主动热情地邀请男人到她的房间去。
男人如约而至。
和所有的情人一样,他们在酒店的床上相互以身体抚慰对方。她几乎爱上了这个男人。天亮的时候,男人离开,没有留下一句话,甚至姓名也没有告诉她。这是不折不扣的露水情人。她还留有对一夜美好的幻想,直到她看到夹在一本书中的二十美元!
她的自尊心受到致命一击,美与美感全部被这微不足道的二十美元碾成齑粉。她的尊严也因此被撕碎,在此后的很多年里她不得不面对时常想起这一幕时的耻辱痛苦。
她从小岛返回,又回到了她熟悉的日常生活。丈夫与儿子让她满意,唯有女儿的宗教狂热令她有些忧虑。她的身体回来了,魂魄却留在了那个岛屿那个房间中。丈夫感知她的变化,无能为力地问她缘故。她推脱是因为女儿,并且在卫生间重新抽起了戒掉许久的烟。

《霍乱时期的爱情》书封
与丈夫的欢爱场景以及因为婚姻生活的烦闷而抽烟的场景,我们在马尔克斯的名作《霍乱时期的爱情》也同样看到过——而这部小说则是他根据自己父母的爱情故事创作的。或许,母亲的故去,让他重新沉湎往事,让他思考众多如同母亲一般的贞洁女人,究竟如何度过漫长的婚姻生活。小说中这样描写安娜的变化:
首先,从小岛回来的渡轮上,一度痴迷阅读的她“连一个字也读不进去,脑海中都是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这与托尔斯泰的写法如出一辙,另一个安娜在认识伯爵后,返回家中的火车上,也是阅读小说,可是她什么也看不进去。
其次,是她一进家门,她就惊恐地询问家里是否发生了什么灾难。这是她心里不安的反应,同时也是这一夜对她生命的唤醒与巨大改变的开始。她“还得花上几天才能意识到,真正变了的不是这个世界,而是她自己,她一直在生活着,却从没观察过生活,只是那一年从岛上回来后,她才开始用批判的目光审视自己的日子”。
一句话,她变得更加敏锐更加富有生命的激情了。与此同时,那二十美元仿佛一顿美味上停留的苍蝇,时刻提醒她尊严的受辱。
她虽然害怕,但是又无比期待再见那个男人。或许,普通作家就会将它处理成情人再相见,解开误会的俗套故事。但是,他是马尔克斯,即便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旅程中,也没有失手。
接下来的每年八月那一天,她都在期盼着重回小岛,给母亲坟前献上一束剑兰已经成为某种程式化的行为。她真正需要的是一年一度的自由,将她从琐碎婚姻中解脱出来大口喘息的自由,一种她感到生命力的撞击,她能够掌控自己身体、自我命运的时刻。很难说,那个贤妻良母是真实的自我,还是这一天的她才是真实的自我。她戴着不同的面具,正如尘世中的每个人。在不同的时刻,露出不同的面孔,犹如川剧里的变脸。这种面具的变幻,既是自我保护,也是生命复杂幽微的象征。
随后,她又遭遇了危险的第二任一夜情人。对方是个骗子与杀人犯,这是多年后她从新闻中获得的消息。
再下一年,马尔克斯会为她安排什么样的情人呢?不不不,他依旧出人意料,依旧保持大师的水准。他让她盼望着,却失落。这一年,她颗粒无收。
继续往下,她在八月的那一天与自少女时代起就爱慕自己的法学博士相逢。一位老朋友,很容易丧失边界跨越暧昧。然而,她控制了内心蝴蝶的荡漾。
此后,她还遇到过一位绅士,希望与她保持长久稳定情人关系的男人,一位给了她名片的人。她将这种毫无神秘感的未来连同那张名片一起撕毁。她要的是不同的男人带来的不确定性。
她甚至还遇到过一位自称“主教”的正派男士,自然是真假难辨的,她也没有探寻的欲望。她在这种激情的催化下,因恐惧与嫉妒,转而怀疑起自己的丈夫。她逼问丈夫,直到丈夫真的招供出一份久远的艳遇。她却失控了,因为嫉妒也因为受辱。她想起第一个男人留下的二十美元,问她丈夫有没有给情人钱……
当然,那象征自由也象征屈辱的二十美元最终被她在一次扫墓后成功花掉了。但是,那笔钱却永远无法从她的脑袋里花掉。她追问丈夫会不会和同一个女人睡觉——这是她不能容忍的事,在此,我们很容易想到昆德拉的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的一段话:
“跟一个女人做爱和跟一个女人睡觉,是两种截然不同,甚至几乎对立的感情。爱情不是通过做爱的欲望(这可以是对无数女人的欲求)体现的,而是通过和她共眠的欲望(这只能是对一个女人的欲求)而体现出来的。”
这段话就是安娜追问的心理动机。
最终,在最后一次扫墓后,她无意间发现了母亲的秘密——“直到此时,作为女儿的她终于大致明白了,原来在去世之前的六年里,母亲也曾怀着和自己一样的激情一次次踏上旅程。”她和母亲的相似性,让她理解了母亲,至此也完成了一次真正的生命之间的对话与理解。
她做了个惊人的决定,将母亲的尸骨迁移。这意味着,她不再苦苦想着那第一个男人,也不再抱有重逢的期待。她明白了他出现的意义。她将装有母亲遗骨的袋子带回了家。小说至此结束。根据编辑手记,马尔克斯似乎对此非常满意。
与以往他作品中繁复的结构与无尽的诗意略显不同,这部遗作几乎可以称得上素朴而克制。作家没有对安娜的所作所为有过哪怕一次道德审判,他甚至为她说出了这样的话:在这样一个男权时代,做一个女人真难。
这是一部以女性为中心,以女性为视角的小说,小说集中探讨了自我发现与自我欺骗之间的博弈,以及婚姻的真相。一切看起来完美的婚姻背后,都有千疮百孔的伤疤。我们借助马尔克斯令人惊叹的创造力,他那旺盛如热带植物般的诗意语言,得以窥见大师最后的慈悲与思考——对女性的爱与理解,对亲密关系的宽容与谅解。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